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新华社供图)
执教国学院
1926年7月7日,吴宓一接到陈寅恪抵京的消息,便搭人力车匆忙赶往西河沿新宾旅馆见他,不想他刚好外出。一直等到下午5点,吴宓终于见到这位阔别五年的老友。两人一直谈到晚上10点,兴奋不已的吴宓随后还赋诗一首赠送陈寅恪:“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
吴宓的激动不难理解。自1919年在哈佛校园结识陈寅恪以来,吴宓便对其博学称赞不已,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谓全中国最博学之人。”1925年初,吴宓被聘往主持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后,便为聘请陈寅恪而积极奔走,如今,他终于来了。
清华国学院的设立,肇源于“五四”之后不断高涨的“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呼声。继北京大学1922年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后,在胡适的建议下,清华筹建国学院,并于1925年9月9日正式开学。
清华国学研究院在风格上兼取中西之长:一方面效仿牛津和剑桥,实行导师制的教育模式;一方面学生在开课时要向导师行拜礼,又有古代书院的遗风。在这一以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之国学专才的独立研究机构,开设的课程分“讲课”与“专题研究”两种,普通讲课外,学生可以自选研究题目,由特定老师指导。
1926年9月,刚到国学院的陈寅恪开设的普通讲课题目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专题指导则包括: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央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文比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从这份课程清单便不难看出,陈寅恪在游学阶段所受海外汉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将之概括为德国传统:强调语言、语文学,认为研究历史脱离不了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对古代文明历史语言的研究。尽管在他看来,陈寅恪开设这些奇怪的课程在当时不无好胜争强的心态:“陈先生是一个很自负的学者,好胜心也很强,而且他那个时候才三十岁出头还没结婚,他在中国这个完全是老辈学者的圈子里边,要体现他不一样的学养。”
陈寅恪学问精深,但对于程度不太够的学生来说,接受起来并不容易。国学院学生姜亮夫回忆道:“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听寅恪先生上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非常苦恼。”

王国维(FOTOE供图)
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北京,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忽失其二,备受打击。陈寅恪原拟增聘的章太炎、罗振玉和陈垣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到任,后继无人的国学院,不得不在1929年下半年停办。陈寅恪自此改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合聘教授,并在哲学系开课,横跨文史哲三系。
起初,他为中文系开设“佛经翻译文学”,为哲学系开设“佛典校读”“中国中世纪哲学史”,为历史学系开设“《高僧传》之研究”“唐代西北石刻译证”。虽然这些课程较之国学院时期难度已有所降低,但学生仍不能适应,陈寅恪不得不继续调整课程。1934年,清华大学文学院代院长蒋廷黻在总结历史系近三年概况时说:“国史高级课程中,以陈寅恪教授所担任者最重要。三年以前,陈教授在本系所授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近年继续更改,现分二级,第一级有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第二级有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及隋唐史专门研究。第一级之二门系普通断代史性质,以整个一个时代为对象;第二级之二门系Seminar性质,以图引导学生用新史料或新方法来修改或补充旧史。”
回顾陈寅恪在国学院数年间的教学,尽管有人认为其课程艰涩,实际影响不大,可在陆扬看来,陈寅恪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开设了哪些课程,更在于“从学术的角度,开创了一个中国学术跟域外学术必须融合的模式。让大家知道研究蒙元史还要了解域外,研究突厥还要了解西方人对突厥碑铭的研究,包括像研究吐蕃和古代藏文之间的联系。在他之前没有人关注这些原始语文、古语文献,只有陈寅恪真正地开始研究,之后影响越来越大。”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7年6月2日,据吴宓日记记载,当天晚上,他正与陈寅恪在家中闲谈,遇到王国维的学生,也是国学院助教赵万里来找王国维。据称,王国维早晨出门后,一直没有回家,引起家人担忧。吴宓当时的反应便是:“宓以王先生独赴颐和园,恐即效屈灵均故事。”不久有人来报,王国维已在上午10时至11时之间,投排云殿西鱼藻轩前的昆明湖中自尽。

吴宓(FOTOE供图)
吴宓当时为何会有那样的反应?翻阅其那段时间的日记,可以屡屡看到他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相聚聊天的记录,虽然聊天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知晓。吴宓在4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师,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王国维当时在想些什么呢?人们后来在他身上口袋中发现遗书,上面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早在1924年11月,冯玉祥派兵将逊帝溥仪驱逐出宫,王国维在这场“皇室奇变”后,便与柯劭忞、罗振玉相约赴难共死,后来未果。这次,在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进逼北京时,他终于一死,被认为是以明心志。
王国维自沉当天,陈寅恪便写了一首七律哀悼:“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并为其撰写挽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姜亮夫回忆:“当天晚上殡葬后,研究院师生向静安先生最后告别。告别会上有两件事我一辈子不能忘:一件是我们二十几同学生行鞠躬礼,但陈寅恪先生来后他行三跪九叩大礼。”
几个月后,感到“意有未尽”的陈寅恪,又为王国维写下一首七古长篇《王观堂先生挽词》,详述王国维生平学术际遇。在这首挽词的序言中,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死亡从殉清升华到殉传统文化:“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心安而义尽也。”
1929年6月3日,王国维自沉两周年,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师生在校园内工字厅东南为王国维树立纪念碑。碑文正出自陈寅恪之手,陈寅恪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日后同样可称夫子自道的文字,自此广为流传。
陈寅恪何以对王国维之死如此念念不忘?两人在国学院的相处时间虽然短暂,事实上交往影响却至为深刻。与陈寅恪“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在回忆文章中曾说过:“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
如挽词所言,陈寅恪自称与王国维之间的关系“风义生平师友间”,两人在东方学的研究中更属同道。陈寅恪在巴黎结识汉学大家伯希和,正由于王国维写信介绍。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仍不断提及两人在学问上的切磋与交谊。1929年,他在《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中据新出的蒙文和满文本改正王国维文章中的错误时,便说:“今寅恪以机缘获见先生当日所未见之本,遂得释此疑。若先生有知,亦当为之以快也。”1927年7月6日,吴宓抄录的陈寅恪《寄傅斯年》一诗中,有“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一句,据史学家余英时考证,这是有感于王国维之死而发。在余英时看来,那种“人琴俱亡”的哀痛,对其从东方学立场回归史学立场,不无影响。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哀悼,仅仅源于学问上的投契莫逆吗?结论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胡文辉在《陈寅恪诗笺释》中对其历年诗作均有详细注解。他注意到在辛亥革命后,在陈寅恪笔下屡屡出现“故国”的字眼,如1927年《春日独游玉泉山静明园》中“园林故国春芜早,景物空山夕照昏”,还有1932年《和陶然亭壁间女子题句》中所谓“故国遥山入梦青”。胡文辉据此分析:“称‘故国’,可见陈氏多少有遗民心态,此心态尤其表现在挽王国维诗及联语中……陈氏的遗民心态自与其身世有关,其父陈三立早年投身变法,但辛亥革命以后以‘亡国人’自居。”其实不仅是胡文辉,当年胡适等人也都谈到,陈寅恪有“遗少”味道。只是,这种心态在北伐之后渐渐消失。
一为遗老,一为遗少,自此似乎不难理解陈寅恪与王国维之间的深沉情愫,也不难理解,何以在王国维的殡葬仪式上,行三跪九叩大礼。但这并不妨碍两代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先生要显示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新的人,比很多人思想都要激进。但他个人一再表示:新不是表面的,可以是最传统的东西,但表现出来我的心灵是自由的。他认为文化形式很重要,一个人思想可以很新,但不能没有自己附着的价值体系。”陆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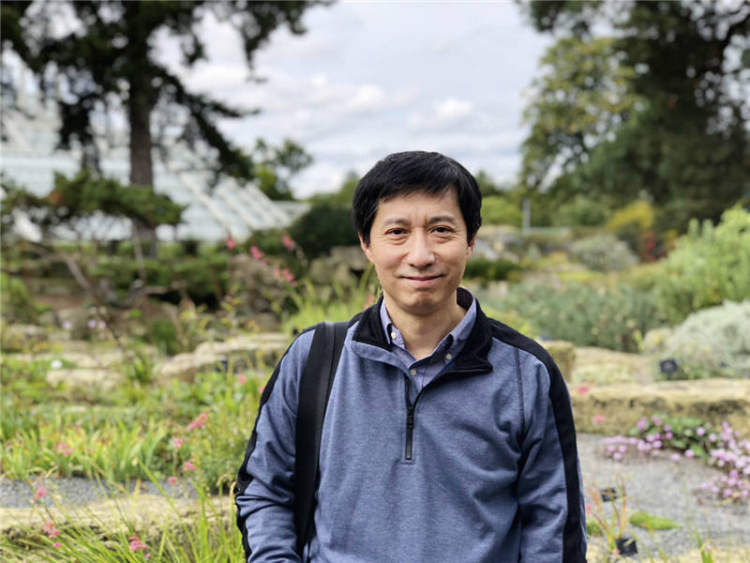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
可资讨论的,还有陈寅恪当年为清华大学入学所出国文试题引起的争议。1932年8月初清华大学及研究所招考新生及转学生,陈寅恪受邀出国文试题。试题由作文题和对对子两部分组成。作文题目为“梦游清华园记”,各年级学生另有不同的对对子试题。一年级的对子上联为“孙行者”。尽管对对子部分只占总分数的十分之一,但由于一年级考试最为重要,加上“孙行者”本身的通俗谐趣,使对对子成为备受质疑的社会话题。为此,陈寅恪不得不接受北平《世界日报》访问,就此公开答辩。后来,他还将对对子的意义再加发挥,以《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的形式发表在同年9月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
在这封写给刘文典的信中,陈寅恪写道,对对子不但可以测验考生对词类的分辨、四声之了解、生字及读书多少,还可以测验思想条理。因为“凡上等之对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直到晚年编定自己文集时,陈寅恪还为此信加了一段附记,指出“孙行者”一联最理想之答案为“胡适之”,并加一转语:“又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复新游苏联返国故也。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
陈寅恪多有敏思捷才,他曾戏称国学院学生为“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在接到1928年刚入主清华的罗家伦赠书《科学与玄学》后,当即便以一戏联相赠:“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方。”然而,在新文化不断高涨的30年代,他以对对子的传统方式作为大学入学考试试题,却可见他“以旧扬新”的自由精神。
“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学者。像梅光迪、吴宓,包括后来在北大任教多年的汤用彤,他们都代表真正在西方受过研究训练的学者,但回国以后,他们强调只有对传统文化真正深入了解,才能对西方的文化有所了解……用传统来表现一种前卫的意识,这是中国19世纪以来一大思潮。30年代以后,中国的西化加深,而且马克思主义进来,这套方式就被抛弃了,新旧之间断裂越来越厉害。”陆扬说。

梁启超(FOTOE供图)
不古不今之学
陈寅恪早年即矢志于史学。1923年,在那封后来广为征引的《与妹书》中,陈寅恪便写道:“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一佛教。”对于佛教,也如俞大维所说:“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和思想的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
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似乎从一开始便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热忱。余英时曾概括其早期史学研究的重点:“我们大致可以说,从1923年到1932年这10年间,陈寅恪的史学重点在于充分利用他所掌握的语文工具进行两方面的考证:第一是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二是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这些“塞外之史、殊族之文”,虽属于当时欧洲东方学中的显学,却也能清晰地看到陈寅恪早年所受晚清西北史地之学风气的感染。有意味的是,中国西北史地之学与欧洲东方学的历史背景相同,都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向亚洲的扩张,前者更可以说是为抵抗帝国主义发展而来。陈寅恪对此早有清醒认识:“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
1927年冬天,著名藏书家李盛铎保存的7000麻袋内阁档案,因为存放困难急于出售,陈寅恪知道消息后,敦促国学研究院购入这批史料加以整理。这批档案原为清内阁大库所存,宣统年间流落出宫,除北大得一小部分外,其余7000麻袋由罗振玉购回,后因财力不足,转售给李盛铎。清华国学院在王国维去世之后,预算压缩一半,无力购买。当时盛传日本满铁公司也欲购买这批档案,后来燕京大学也加入了购买行列,一直对此保持关注的陈寅恪,又敦促1928年10月刚刚成立的中研院史语所买下档案。在1929年2月2日给所长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写道:“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
正是在陈寅恪与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下,史语所最终以两万银元的价格购入这批内阁档案。史语所成立之后,陈寅恪被聘为研究员,并兼第一组历史组主任。傅斯年希望他可以就近在北京负责整理内阁大库档案。
然而,陈寅恪在上世纪30年代初,逐渐将史学研究的重点转入“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也就是他1933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说,“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余英时分析转变背后的原因,认为与其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的追求不可分割。陈寅恪清楚,以“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东方学而言,欧洲已形成有规模的传统,后起者除了在某些“点”上寻求新的突破,很难取得典范式的成就。况且,王国维去世后,国内能相与讨论的知音渐稀,也是不争的事实。此外,在余英时看来,陈寅恪的史学转向与20年代末期流行于中国的两股史学思潮也不无关系。
1929年5月,在给史学系毕业生的两首赠诗中,陈寅恪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在前一首诗中,陈寅恪感慨于中国史学的衰落,致使史学系毕业生要纷纷到日本进修中国史。余英时考证,诗中田巴、鲁仲分别代表国内两派史学潮流:胡适“整理国故”一派和唯物史观学派。陈寅恪显然对这两派都有所不满,“1929年以后,他转入中国中世史的领域,一方面固然是‘不甘逐队随人’,故不惜向东方学告别,但另一方面则未始不是由于他要发愤自出机杼,以多方面的创获来示人以史学的‘真谛’”。

作为清末的世家子弟,陈寅恪对晚清历史异常熟稔,但他对此显然有所回避。一次,他对自己的研究生刘适说:“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只是,以诗证史,以沉痛家国兴寄为史为文,一直是陈寅恪的文章风格。他如何来平衡历史研究中的有情与客观?对我的问题,陆扬的回答是:“陈寅恪是一个历史中的人。研究历史的时候,他始终觉得自己既是历史的一部分,又是对历史的回应者,这两个角色在他身上始终是交融的。他对古人有‘同情之了解’,而非‘了解之同情’,前者是回到古人的世界,以他的喜怒哀乐构建他眼中的世界;后者是研究以后,发现我喜欢古代的人物。他在这方面极其冷静,在这个意义上,陈先生更符合我们今天的西方历史研究,而不一定是19世纪初、20世纪那套科学的办法。”
在清华园的10年间,陈寅恪大约发表了50余篇学术论文与序跋。用汪荣祖的话说,他后来在战时发表的书与文,其研究工作已在此一阶段完成。其中,《李唐氏族之推测》《支愍度学说考》《读连昌宫词质疑》《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等重要论文,已为陈寅恪后来几本专著写作奠立基础。
(本文写作参考汪荣祖《陈寅恪评传》、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吴学昭《吴宓和陈寅恪》等专著,余英时《陈寅恪史学三变》等论文。实习生纪之湄对本文亦有贡献)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