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9——
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坎藏区,上世纪80年代出道文坛。十余年前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让他荣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作为小说家,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自道),阿来在文坛的地位早已尘埃落定:无疑,他是当代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藏族作家。作为电影《西藏天空》内核的架构者,编剧阿来似乎才是这部电影“最大的西藏元素”。作家转做编剧,很多是为生计所迫,但对阿来而言,严肃文学出身的谱还是要先摆一摆的,“我个人是比较讨厌做电影的,所以一开始让我写剧本的时候我拒绝了。后来,他们拿了一个七易其稿的剧本给我,我看了也很失望,然后修改,开始给剧本找亮点。”
6月19日上午,上海影城《西藏天空》的放映场座无虚席。当影院的灯光亮起,全场掌声雷动。在笔者二十多年的观影经历中,观众自发给一部主旋律故事片如此礼遇,之前似乎只有王铁成的《周恩来》、李雪健的《焦裕禄》以及刘佩琦的《离开雷锋的日子》。在影迷主创问答环节,一位中年职工模样的上海人把提问变成了个人情绪的宣泄与演说,他曾经支援过西藏建设,被电影展现的画卷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也是一幅当下主流观影群体90后们不能理解的图景,身旁一位上海朋友轻轻地告诉我,这让他想起了当年在五角场看谢晋电影《天云山传奇》的热络气氛。
无暇去展开一部主旋律电影得失成败的探讨,但刚才列举的那几部电影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角儿”的戏。从这个角度说,《西藏天空》无疑是一次冒险:西藏故事,藏人编剧,99%藏人演出,全藏语对白!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告诉笔者,“1949年后,我们拍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影片。但这些片子,充其量只能算是‘少数民族题材的汉族电影’,而无法归入‘少数民族电影’的序列。它们在叙事风格上缺乏一种少数民族的主体性。所谓藏族电影,并不是从藏人的角度来讲述自身,而是从其他民族,或者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述西藏。在这种讲述中,西藏和藏族是一个他者,而不是主体。”
藏人出演,藏语对白,是《西藏天空》不类他者最显著的特色。电影讲述了两位西藏青年——庄园主的少爷丹增与朗生(家奴)普布之间的恩怨情仇。丹增与普布从小在一个庄园长大,因少爷犯错,农奴险些丧命。之后为了替少爷赎罪,普布以少爷替身的名义到寺里修行,将少爷的名字作为法名,所念的经文、所修的福报,皆为少爷所有——这对经典的“替身”结构,让人想起了不少老电影,比如《铁面人》和《佐罗》。“替身”关系往往意味着尖锐的阶级对立与固化社会的宿命安排,但将这一关系的时代背景放置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西藏和平解放前,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那么这对小伙伴命运的轮转,又岂止是天翻地覆所能尽述?
《西藏天空》也是国内第一部借鉴外国文艺片发行模式的电影,于4月15日在上海率先点映,在没有任何官方组织观看的情况下,上映一个月票房六百万。回到文章开头,6月19日上海电影节期间公映一场更是一票难求。笔者看罢在朋友圈发言,“翻身农奴得解放,在阿来及电影主创的诠释下被锚定在‘解放意味着平等与尊重’的普世价值上。消解掉意识形态的宣教,解放不是被动地布施,不是一个大救星换位一尊神佛的普照,而是寻找自我、认识自我、肯定自我的价值启蒙。”
本文发稿前,笔者再联系他,希望作为高原摄影家的阿来提供几张藏区的摄影作品。电话那端的声音伴着粗粝风声,他说自己正在高原为自己下一部电影选景呢,得等几天回成都后再说。
当年他办杂志发行量可以过百万,老本行写作则让他成了很多作家富豪榜上的常客,看来第一次“触电”后,多少也会有些乐此不疲了。至于第一次尝试非虚构写作的作品《瞻对》,他说自己并不愿意画地为牢,“我干嘛要框定自己就是写作什么的?写作本来就是件随物赋形的事情,有些题材适合写成小说,有些题材适合用报告文学表现。”
而对近日《瞻对》在鲁迅文学奖评奖的零票事件,阿来只回应了三个字,“很荒诞。”
阿来口述
解放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平等
这个剧本惟一的亮点就是一开始两个人互为替身那段。过去西藏的一些有钱人家觉得自己的身份高,有什么吃苦的事就找穷人家的孩子代替自己的孩子去,比如出家。甚至在满清晚期,政府到西藏地区办学校,藏人贵族都会找穷人家孩子代自己的小孩去。
在剧本里,丹增是贵族家的小孩,丹增并不是个贵族姓氏,一般藏民也可以这么叫。普布是个朗生,朗生是西藏社会最低的阶层,就是家奴,人身和财产完全归属主人。过去在西藏,这种人很少,我估计只有百分之一二十。他们终身要依附于主人家过活,也有朗生后来获得了自由身,比如说他去帮主子打仗,立了战功,或者主人家比较善良,在做过多少年以后还他一个自由身。朗生的爱情生活也会受身份的影响,由于等级森严,而且家奴也是世袭,只能在同一阶层内部解决婚姻问题。
我生在西藏,长在西藏,不用专门为了电影特地回去如何如何考察,我什么都知道(笑)。我们当时只是在藏区走了一圈选景,西藏这几十年的变化太大了,要复原当年的场景很困难。比如剧组需要一个贵族庄园的场景,今天就怎么都找不到,现在新修的镇子完全是汉式建筑。
电影以1946年的一个历史事件开始。那个时候的西藏反对一切变化,但当时西藏跟在印度的英国人关系比较密切,英国人在西藏有一个驻拉萨商务代表,这个商务代表建议在西藏建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学校。西藏的少数改革派同意了这个建议,就从印度和尼泊尔请来了教师,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都可以去读书。当时招了四十多个学生,后来学校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抗议,所以只办了半年时间,有据可查,学生们在上学路上经常被拦截、威胁。丹增上学去,普布就跟着,帮他背着小黑板——当时的小孩上学很少用纸,传统是自己背一块小黑板。丹增上课,普布就站在窗子外面听。
学校关闭以后,两个小孩儿就整天无所事事在一起玩。有一天,普布惹出事了,冒犯了喇嘛,作为惩罚,要挖掉他的眼睛。怎么挖?在给人犯用刑时,给人犯戴上一个数十斤重的石帽,然后两人持棒骨分别用力抵住两侧太阳穴,再上下左右挤压下去……不一会儿,人犯的眼球向外突,然后拿专用工具轻而易举地把眼球挖出来。丹增为救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他代替自己出家修行赎罪。当时西藏有很多希望改变的贵族家庭会把子女送去外面读书,送到印度甚至英国。所以两个人就分开了,一个在寺院里接受传统教育,一个人到印度接受现代西式教育。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就到了解放军进藏,两个人也都长成了十几岁的少年,再见面就再会有故事,有的时候他们互相怜悯同情,有的时候又互相尖锐地冲突。他们一同经历了“文革”,最后到了80年代。
我反对狭义地理解翻身农奴得解放。在我看来,解放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平等。真正的解放是对所有人的解放,大家都得到了平等,然后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再去发展,去竞争,然后一起生存。
我1959年出生,本名叫杨永睿。父亲是回族,母亲是藏族,他们一直相处得很好。父亲出生在商人家庭,上过一些私塾,后来参加了解放军,打了很多年仗。因为出身问题,转业后做了农民。我出生在大渡河上游梭磨河畔一个藏族寨子里,叫马尔康。马尔康在方言里有“光明之地”的意思,也是“油灯很多的地方”。因为那儿有一个寺院,寺院里油灯很多。拉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就有一个小电站,从印度进口的,建在布达拉宫,专门给贵族和达赖喇嘛供电。拉萨大规模的供电是在解放后,之后才遍布藏区。
我是家中的长子,但从小就有一种孤独感。在村子里,大家都很穷,但支部书记家的孩子还是有些意气风发,似乎是“上等人”。人对区别性的对待很敏感,我总觉得会被另眼相看。村子在解放前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驿站,有很多生意人,种地的倒不多,来往客商也不少,所以我从小就懂一点点汉语,而且我父亲是回族嘛,也讲汉语。但上学后,突然接触到那种规范的汉语,还是有点无所适从。我是“文革”时上学的,学会的第一句汉语便是“毛主席万岁!”学校里讲的一些抽象概念我们也不懂,“文革”期间的语文课就是政治课,天天念报纸上的文章,讲阶级斗争。我在一个小乡村中的生活经验,跟书本上呈现的生活经验完全无关。
但我比较聪明,有一天恍然大悟。那是小学三年级某一天,我听懂了老师的一句话,对书上的道理和它背后的逻辑一下就开窍了。我喜欢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可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也不鼓励学生去质疑,后来我觉得自己不用上学了,只要不断地看书,问自己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我想懂的事情,我都会懂。
我也做过中学教师,自己都心生讨厌。除了鼓励甚至压迫学生死记硬背,学校教育不做第二件事。大部分人会接受现实,但我觉得好不容易上个学,应该不仅仅为了考试。考试太容易了,我跟同学一起背课文,他们要用一个星期,我只用两个小时。但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会焦虑,有些问题搞不明白,甚至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开悟了,这时如果再让我看什么书,即便老师没讲过,自己也就懂了。这个习惯造成了我后来学习上不是特别依赖老师。到了中学以后,老师们对我持两种看法,有一些很喜欢我,觉得我聪明;有些觉得我自作聪明,极其讨厌。
小学就在自己村子里,很简陋的一所学校,接触外边的人很少。当地质勘探队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好神奇,他们是我最早看到的除了军人以外穿制服的人,蓝色的工装,宽檐儿的白帽子,而且带着很多仪器,随便照一照就能知道到山顶的距离,探一探就知道地下有什么东西!他们住在村边的帐篷里,在我看来特别现代化,我经常跑过去听他们聊天,一会东北大兴安岭,一会新疆吐鲁番,嘿,都是没听过的地方。
那些人也跟我们小孩儿聊天,聊的过程中觉得小孩儿里有一个跟别人不太一样。有一天,有人拿了一张航拍地图给我看,说“小鬼,来找找你们村子。”我们那村子很小,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但分布在二三十公里长的山谷里。从地理上来讲,村子是很大的了,有森林、有牧场、有雪山、有耕地。我可以上山去放羊,到地里种庄稼,跟比我们大的年轻人去打猎,这样的生活很精彩。但当那个人让我在这张航拍照片上找找我们村子时,只见一座座山像一个个小褶子。那人指着其中一个褶子说,喏,就在这!可我趴上去看,一座房子也找不到。我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很大,太大了。我本来觉得自己的村子已经很大了,从这里去到下一个村子有时要走上一整天,但在这张地图上它只是大山褶皱中一条褶子上的一个点。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来到了省城,在中学里教书。经常听到新华书店来新书的消息,不知道是什么书,反正书店没开门就得去排队,一开门,进去见书就买。那时,图书市场开始解禁,可能今天卖的是托尔斯泰,明天就是中国古代某个作家的书,大都是“文革”前出过的再版。见书就买,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其实家里书早泛滥成灾了。那时我也去泡图书馆,有些书“文革”被封起来,多少年都没人动,一翻开先呛个喷嚏,就如饥似渴地读。整个八十年代,别人急着写点东西,我却在大量地读书。书都读不过来,有什么可写的啊?
那时对于我来说生活里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书店里来新书了,一个是影院来新片了。片子有很多,也是解禁,很多译制片,“文革”前拍的故事片,甚至还有解放前拍的片子——《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赵丹、孙道临。
《西藏天空》的本子,我是用汉语写的。藏语对白是导演的功劳,这是值得鼓励的。整体的语感其实连着语境——别让我举例子——这就是一个整体,一种味道,没法拆开说都有什么。其实我一直认为外语片子上字幕就行了,不用译制过来,用一种中国人自己想象的外国人很夸张的说话方式去表现,虽然译制片也有明星配音,但我听起来总是不自然。现在一部电影DVD当中就会出现几种语言的转换,在哪个地方就用哪个地方的语言,我相信这样更自然。
这七八年,我经常在青藏高原行走。本来是所谓在做人文关怀,但我逐渐发现大自然很美妙。我不拍人和风景。尤其是人,现在所有人都拿着手机在拍(笑),尤其是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拍起来更肆无忌惮。我觉得拍别人需要巨大的勇气,拍模特除外,穿了,脱了,都是让你照的(笑)。
尤其在5·12地震的时候,我深入灾区,发现很多人啥事不干,就是在那儿拍别人。在北川,我曾看到一家人在恸哭遇难的亲人,旁边竟然有七八个长枪短炮对着他们,我觉得这很不尊重死者和生者。至于风景,现在青藏高原交通便利,能拍风景的地方遍布人的足迹,不知道被拍过多少次了。
人们经常说热爱大自然,但大自然都有什么?我就开始学习植物学,同时结合野外观察。为了记录植物的影像,我买了很好的相机。我也随身带着笔记本,记下我当时的心情和这些植物相关的背景知识,如当地的气候、物候、海拔、地质,你会发现不是所有植物都会在一起相处,只有那些相关的植物才会形成一些群落。我现在拍的植物的照片已经有几万张了,形成了一个青藏高原的植物影像库。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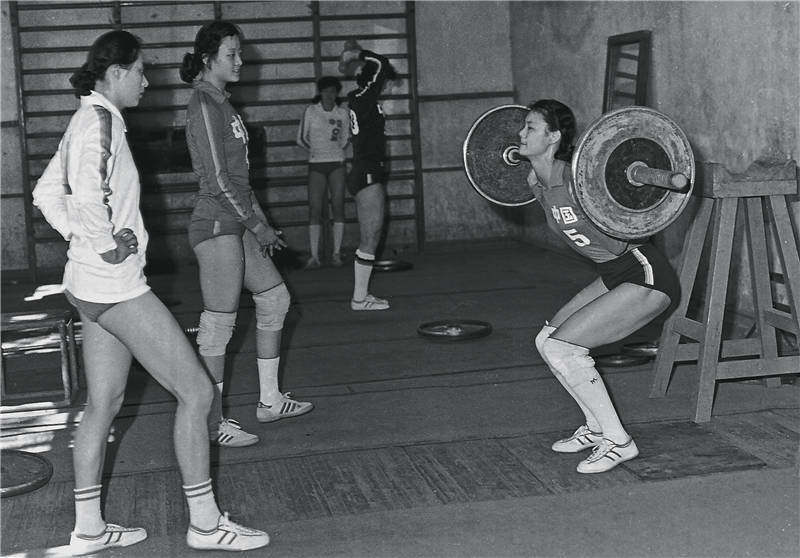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