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眼”之父南仁东(新华社供图)
宁静的奇观
2017年9月15日,天文学家南仁东因肺癌离世。去世后的宣传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这位科学家和他倾尽一生的“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由中国自主研发,坐落于贵州省平塘县。南仁东生前是这一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射电望远镜的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
同事们的回忆中,这位老人给人留下随和的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筹划FAST项目后,每次到贵州,他都到工地上,随意地穿着大汗衫和工人们蹲在一块儿聊天。许多访客一下分不清谁是民工谁是南仁东,只有鼻梁上的眼镜暴露着他的身份。“他记得许多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干哪个工种,知道他们的收入,知道他们家里的琐事,他对工人的那种尊敬,要不是亲眼见过,绝对难以想象。”FAST工程调试组组长姜鹏在此前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人们想寻找他的传奇经历,却发现南仁东的一生相当“平淡”。他也遭受磨难——生命的最后几年,南仁东罹患癌症,拖着病躯在贵州与北京之间来回奔波,项目中遇到难题,也曾几天几夜睡不下觉。不过总体上这位随共和国一起成长的科学家的人生十分顺利,1963年以吉林省理科高考状元身份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在吉林省通化市无线电厂富有成效地做了十年工程师,积累了工程和社会生活的经验。1978年恢复高考,南仁东考上中国科学院王绶琯院士的天体物理研究生——不同于常见的命运阴差阳错的桥段,夫人和领导开明地支持他,厂里特意安排人出差送他前往北京报到,同事说他上车后不舍地“一路哭到锦州沟帮子”。南仁东随后一直在中科院任职,其间多次到海外交流访问,一切仿佛都在为他日后完成FAST项目而准备。甚至画画的爱好都有用武之地——FAST徽标就由南仁东亲自设计。
FAST工程也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按照工期顺利完成,2016年9月25日正式竣工启用。南仁东在生命最后一个月,见证了FAST带来的中国射电望远镜脉冲星发现零的突破。南仁东和FAST,是一出皆大欢喜的圆满故事,在工程奇迹屡创世界第一的今日中国,似乎成为锦上添花的点缀。
然而巨大的波涛正是在平静中酝酿。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仅没有,而且从未曾打算自主研发一台大口径射电望远镜。这项工程耗资甚巨,却不像军工、医疗一般关系“国计民生”,虽然是天文学研究,但其主要关注宇宙起源与演化、天体结构、地外生命等,因太过基础也不会短期、直接地应用于载人航天、空间站等人们熟知的航天项目。在FAST工程介绍中,南仁东直言,FAST是能力超强的望远镜,但能看到什么,以及看到的东西“有什么用”,在建成前并不完全清楚。FAST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奢侈品”,也正因此,它是“国之重器”,而且只能是“大国重器”。
如今的FAST,坐落在贵州大山深处,整个工程颇为壮观,500米口径的“大锅”接收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FAST的灵敏度极高,其探测极限是1×10-30瓦/(赫兹·平方米),可接收到137亿光年外的微弱信号。为避免干扰信号,贵州省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电磁波宁静区,限制附近人类活动,迁移了FAST上空航线,甚至专门立法关闭周边数公里内所有通信基站。在FAST附近,不仅拨打手机被严格禁止,数码相机也不允许使用,汽车不能使用电子打火。
无论在可见还是不可见的世界中,这座庞然大物都处在绝对的宁静中,等待着来自宇宙最深处的信息。如南仁东所说:“大口径望远镜的建设不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它来源于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 FAST标志着中国人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好奇目光,看向宇宙。

2016年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落成启用(新华社供图)
大口径方案
1993年,东京召开了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各国科学家一起筹划21世纪的射电天文学发展蓝图。科学家们期望抓住最后的时间窗口,在电波环境彻底被人类经济活动破坏之前,弄清宇宙结构是如何形成和演化至今的,只有大射电望远镜才能帮助人类实现这一梦想。否则,除非人类有能力到月球背面去建造同样口径的望远镜,宇宙起源的许多问题将成为永远的未解之谜。
这样一项大跨度的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是最优选项。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国天文学家提出了共同建造下一代大射电望远镜的倡议,1999年定名为SKA计划。据参与FAST项目的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彭勃介绍,各国方案的思路无非两种:“大口径小数量”或“小口径大数量”——可以一个大望远镜解决问题,但有实力这么做的国家是极少数,也可由相距一定距离的多个望远镜组成阵列,不过仅凭一国很难完成。多数国家赞同小口径方案,中国则倾向大口径方案。
1994年,南仁东初步确定贵州是合适的建造省份,有着天然的喀斯特地貌和安静的电磁环境。他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跋涉,先后对比了1000多个洼地,时间长达12年。结合遥感技术反复搜寻、甄别、分析,从200米、300米到500米口径的“大坑”加起来共100多个。南仁东坚持这100多个都要去走,因为他一定要寻找到一个能够建造最大口径的地点。
南仁东对大口径方案的态度,在当时看来是不切实际甚至虚妄的,1994年中国口径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只有25米。FAST高级工程师甘恒谦在此前接受本刊采访的时候强调,500米口径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超前的想法”。此前200米口径方案都已经被评价为“超级大胆”。SKA国际组织总干事菲利普·戴蒙德(Philip Diamond)也说:“我从未想过这个望远镜是500米口径的。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设计创意的时候,我就震惊了。”
南仁东清楚,万一入选SKA国际计划不成,中国是有可能下决心独立建造一座射电望远镜的,那就必须要求超大口径,才能获得以前达不到的观测数据并在一段时间内领先,否则就没有意义。1994年,他给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写信,请求理解方案设计思路,拨款支持选址工作,周光召特批了5万元,第二年又批给选址组6万元。因为对超大口径方案可能性的坚持,随着选址工作力度加大,他又请求遥感所、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的帮助。1996年,终于发现了大窝凼,这是有可能实现500米口径的地点,后来FAST也正是建在这里。
在90年代中国社会千头万绪的情况下,国家各部门对射电望远镜这样一个没有经济回报,即使建成也至少是几十年后的项目的一次次支持,背后是远见卓识和相当的定力。大射电望远镜的建造带有天然的矛盾性质,其选址要求无线电活动尽可能少——欧洲、日本因此无缘,而不发达地区又无条件,如果独立建造,世界上只有中、美、俄等几个大国有机会。是否抽出精力去做一件“无用”的事,其实是对未来的投资和对自身文明定位的考量。
90年代南仁东个人也经受着考验,作为壮年生逢改革的科技人才,不是没有机会去做更容易“变现”的事情。早在70年代,他就曾改造计算机键盘设计,使企业成为通化市三家盈利大户之一。而当90年代知识分子纷纷下海时,他拿着昔日好友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工资,为一项宏大的事业默默准备。
选址的同时,项目组完成了30米口径索网结构缩比模型等一系列申报准备。南仁东反复说过:“我们还是要争取把SKA引到中国来落地。”从1993年开始,南仁东一直是这个国际计划的中国推进委员会主任,经过十几年的酝酿、申请、评估等工作,2006年夏天,中国代表团到位于英国剑桥大学的SKA总部去参加答辩会,国际评委会将最终决定SKA落地何方。
SKA评选的同年,南仁东当选为国际天文学会射电专业委员会主席,这也是中国天文学界第一次在此层级任职。自80年代中期以来,南仁东先后在多国进行客座研究、联系合作,其学术水平与对天文事业的热爱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尊重。曾有世界知名的天文学家在去世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坐着飞来中国再见南仁东一面。不过对中国天文学界的认可并没有影响到国际评委会基于一系列现实因素的项目选址考量。
2006年9月,国际SKA计划推进工作委员会发布了最后决定,中国落选。SKA项目确定由澳大利亚和南非实施,他们都采取了多国复杂合作的阵列形式。根据澳大利亚的提议,这个阵列将最远延伸至新西兰。根据南非的提议,碟形天线将建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赞比亚、毛里求斯、肯尼亚和加纳等多个国家。
自主建造
在2007年的时间节点上回看,虽然SKA项目建成之后,其性能将会超过其他射电望远镜,但其协调复杂、建设周期长,真正投入要等到2030年底。如果中国单独建设一台大口径射电望远镜,仍能争取到数十年的观测期。但前提是,其口径必须达到500米左右才有意义,这也正是南仁东一直以来做的准备。
国际SKA计划不会放到中国来做已成定数,是否还要花大力气自己建造?如同此前给出的支持,这一次答案也是肯定的。次年,中国科学院即正式申报FAST立项,当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FAST工程正式立项。团队一片欢呼,但据当时的人回忆,南仁东反而是一种无喜无悲的神情。因为他清楚,真正的工作才刚开始。
作为FAST这样一个涉及领域极宽的大科学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和总工程师,南仁东从单纯的天文学研究变成了要懂力学、机械、结构、电子学、测量与控制、岩土等的全才,大家开玩笑叫他“战术型老工人”。动工时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了设计图纸,他迅速指出几处错误。现场的六根百米支撑塔建好后,他第一个爬上去,连螺丝拧得好不好他都十分清楚。他是FAST项目组里最忙碌的一个人,FAST项目工程师潘高峰此前告诉本刊,如果出差没有网络,南仁东就会坐立不安,“因为没办法处理邮件,他每天要处理上百封来自国内外的邮件”。在贵州克度镇大窝凼施工现场,他也总是冲在最前面。“台址勘察的时候,他已经65岁了,跟年轻人一起在没有路的大山里攀爬。在去周边最陡峭的一个山顶时,大家都劝他在山下等着,但他非要跟我们一起去。看到南老师这么大岁数都要亲自上去,搞得几个设计院老总也不好意思了,都跟着爬了上去。”
南仁东在生命的最后10年,进入了冲刺阶段,他一生积累的知识、经验、见识,转化为迸发的创造力。FAST对反射面上空的馈源舱定位精度要求很高,当时团队做过几个馈源支撑缩尺模型试验,一直不能达到最大的观测角要求。南仁东很有想象力地提出,在馈源舱周围加一圈流体或半流体的“水环”,流体受到重力影响集中在某一方向,这样可以有效补偿姿态控制的不足之处,会使馈源舱的角度发生相应变化。虽然FAST最终采用了另一种方案,但南仁东“水环”的想象力确实让项目组其他成员印象深刻。
钢索结构的疲劳问题,对FAST的命运是决定性的,也是整个项目最大一次危机。姜鹏坦言:“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寻找合适的钢索材料会面临如此大的困难。”从知名企业购买了十余种性能最好的钢索结构进行疲劳试验,结果发现FAST对钢索结构的性能要求已经远超国内外相关领域的规范,FAST必须从头开始解决材料的问题。南仁东甚至提出用弹簧作为弹性形变的载体,来解决钢索疲劳问题,让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但这一方案显然太过超前,技术条件不成熟。姜鹏回忆:“我甚至不记得会议是怎么结束的,只记得当时出奇地安静。当我们都离开会议室时,他仍然站在黑板前,背着手看我画的图,那时我觉得他有点无助,像个孩子。”研制工作在涂层改善、锚固技术等几个方向上同时开展,两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近百次的失败,几乎每一次的实验南仁东都亲临现场,沟通改进措施。钢索结构终于被研制出来,一项项技术难关被克服。
南仁东的发小吴学忠曾经回忆,有一年端午节,还上中学的他和南仁东天不亮就爬到龙首山顶去看日出,海阔天空地聊到夜幕降临,他才知道南仁东那时已经酷爱天文,每月必订科普杂志《每月一星》。差不多在他们上中学的同时,1958年中国与苏联的天文学家在海南岛联合进行了日环食观测——这是对太阳射电的研究,迈出了中国天文学的关键一步。吴学忠惊讶于南仁东极其丰富的知识——他能绘声绘色地讲出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意外归来》,讲出《伊凡雷帝杀子》的原名是《1581年11月16日的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在一个看似贫乏的年代,他的所思所想却无比浩渺,正如当时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一起研究了太阳射电后,中国的科学家还想研究太阳系外的事情,这需要有较大的射电望远镜,当时国力还不允许,南仁东后来的研究生导师王绶琯院士就想出替代方案,于1966年提出了在北京市密云县建立射电干涉仪和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方案,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的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南仁东成长起来时的中国,真正建造一个大型射电望远镜已经成为可能。
2016年9月25日成为中国天文学史的里程碑时刻,FAST在这一天举办落成仪式。化疗后的南仁东头发稀疏,一个人从首都机场前往贵州。姜鹏说,当时南仁东其实是有些焦虑的,直到2017年的8月27号,望远镜第一次实现跟踪,收到了跟踪的效果图,他才宽慰下来,向调试组发来了祝贺。不到一个月后,南仁东去世。
90年代考虑参与国际合作项目时,除了贵州,其实天文学界还联合总参谋部、北京大学等一系列单位进行了勘测,提出过以下候选地:川西高原、柴达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内蒙古草原、鄂尔多斯西部高原、青海湖南部地区、浔江冲积平原、大丰—东台沿海平原、河南南阳地区、湖南湘北地区、广西百色地区、广西河池北部区域、柳州—南宁间的盆地与丘陵区域、云南宣威—沾益区域、云南师宗县北部区域等等。这是诞生于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方案,因为这里的人们要看向最深的宇宙。
南仁东主编过一本介绍FAST的科普书,他把解释“为什么需要一座大射电望远镜”问题的章节取名为“迈向星辰大海”。他举了哥伦布远航的例子,无论是哥伦布,还是支持他的大胆想法的伊莎贝拉女王其实都不知道那个新大陆的存在,他们只是抱有一个简单的信念:大船能远航,他们向往远方。书中有南仁东自己写的一首诗,最后几句是:
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
召唤我们踏过平庸,
进入它无垠的广袤。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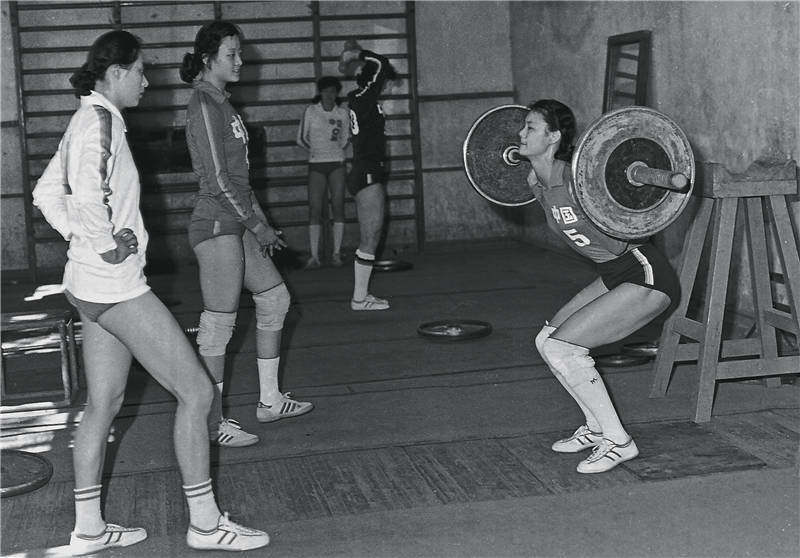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