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和他的作品《试论疲倦》 )
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被定义为文学史中“活着的经典”。他因此更像是一个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人物,想象他的严肃,想象他的愤怒,想象他会因为一个无趣的提问扭头而去,想象他因此并不好相处。以至于,就连这种想象似乎都是小心翼翼地进行的。我们还喜欢给这种想象贴标签,先锋、实验、反叛、后现代以及政治性等等。一厢情愿。直到,汉德克在前些天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中国行,用他温和的方式,在我们面前做出撕掉身上的标签和破除想象的努力。
首先是《骂观众》,这是彼得·汉德克在中国被提问最多次的一部作品。这部他在1966年创作的剧本,使他一举成名。它完全没有遵循传统的戏剧规则,没有情节、对话、戏剧性人物和行为等等,演员从头到尾站在舞台上“谩骂”观众。这种反传统审美的呈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成为他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之一。与之同期进入中国的,还有他同年写作的小说处女作《大黄蜂》——一部同样反传统的作品,一个童年经历战争的人回忆战争中发生的种种,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传统小说不同的是,书中没有脉络清晰且连续的发展情节,更多的是事件的细节以及具体的感受。
对于其早期作品的熟悉及对后来作品的陌生,使得汉德克阶段性的创作风格被很多人想象成了他创作的整体样貌,甚至于他整个人的处事风格。有关愤怒、反叛、实验精神的判断,大多来自于这里。更重要的是,那种反叛精神恰恰与中国读者在接受这些作品时的内在经验和需要不谋而合,形成了很强的认同感。因此,大量的问题不断反复地指向这里。
汉德克打破了这种想象。他否定了《骂观众》的创作是一种语言的实验,创作灵感也不是来自文学,而是他想要写一个作品,用来复制披头士的那首《I Want to Hold Your Hand》里的精神,对当时正在读大学的他来说,它意味着一种解放。《骂观众》就是汉德克用以表达这种精神的形式。他说,这部自己只花了6天写成的剧本,“它甚至称不上正规的话剧作品,更多的是一部完整的话剧之前的引言部分”。
他继而撕掉了提问者给他贴上的“反戏剧”和“后现代主义”的标签。“我创作时,根本没有‘后现代’这个词。”他并没有否认自己在尝试戏剧的最初阶段有意地对传统戏剧做出改变,但这个阶段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极为短暂,仅仅集中在最初的5年,远不能构成一种概括。从70年代开始,他的戏剧创作形式就回归到了经典话剧。他说,直到不久前刚刚写完的话剧,他都是在遵循传统。“综合来说,我的第一批戏剧,或说早期戏剧是一些更友好的戏剧。而我现在的戏剧反而更多的是只具有一种友好的形式而已,而我的内容反而是一些反戏剧方面的东西。”
但问题还是反复,汉德克终于被引入了一种更为符合人们之前想象他的样子,开始对提问表示拒绝:“中国的观众总是抓着《骂观众》这出戏不放,对我来说有一点不礼貌,老追问这一部。这个问题让我感觉像是在问我小手指的指甲,但是我整个人在这里,那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我有很多的作品,那只是我早期的一个小小的作品,我觉得这特别遗憾,甚至让我觉得有一点心痛。”
一路从上海到乌镇再到北京,汉德克在公开场合的回应逐渐显得疲倦。他开始更加明确地表现出自己对问题质量的审度——只有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德语年会上,对于台下的德语研究者们的提问,他表现出了充沛的兴致,一度主动提出“再来几个问题,我们再结束”。——其他的公开活动中,虽然他也会在结束时礼貌地说上一句感谢:“很多人的问题对我来说就是打开了一扇一扇的窗户。”但回答问题时,却完全没有附和跟含混,或还会不时地发出反问,这让现场的气氛有时略显紧张,但这正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态度。
汉德克的政治标签主要来自西方的主流媒体。最早是因为1968年的戏剧《卡斯帕》的成功。它讲述了19世纪德国纽伦堡的一个街边少年,只会说:“我也想成为那样一个别人曾经是那样的人。”人们教他讲话和语法,最后他被谋杀。“对我而言,杀死他的那把刀就是语言、语法,这部戏的主题可以理解为语言是可以杀人的。”汉德克说,“这部戏首演的同一天,发生了大学生骚乱。于是整个欧洲批评界对这部戏的反应都是充满热情的,媒体当时说,这部戏就像是为巴黎街头的大学生们创作的一样。”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表达一个主题,就是一个青年人是怎么被社会毁掉的。”汉德克说,“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很具政治性的人,基本上我写作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来自于社会上大多数人参与的运动。”至少在《卡斯帕》时,他就并不是主动进入社会活动的公共视野的。
人们再一次开始从政治的视角审视汉德克,是在90年代。不再是充满热情,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攻击,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标签。汉德克回忆说,攻击集中在他1996年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后,这篇文章当时被全文刊载于《南德意志报》上,记述了他在1995年底在塞尔维亚的旅行。通过自己的观察,他描述了南斯拉夫解体后的现实,并将矛头指向西方主流媒体无视事实的一系列报道。“(文章发表)之后的四周,一片死寂,而后骂声一片。”很多人站出来批评他。
汉德克说:“要是我不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话,那我的人生中就缺少某些决定性的东西。”他并非拥有很强的政治性的说法依然可以继续成立,那是因为,他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种民族认同感。他的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因此,对于塞尔维亚,对于南斯拉夫,他有着一种很特别的情感。
他没有因为反对而停止发声,而是始终表示自己对于战争的痛恨,对于遭受战争的平民的同情,以及对于西方人道和正义假象的嘲讽。“我无须辩解,但是要让人们听到我在想什么。”当时,已经有20年没有附和德语文学朗读传统的汉德克主动向苏尔坎普出版社提出做一次朗读之旅,以表示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反对。“在人们众口一词地支持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时,却对轰炸所造成的几千平民的死亡视若无睹,在人们批评米洛舍维奇对于平民的屠杀的同时,却忽略了北约的轰炸也是对平民的屠杀,同样是一种不顾民意的专制暴行。”
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至科索沃。同年,他的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表示对德国军队轰炸的抗议,汉德克退回了自己在1973年获得的毕希纳奖,这个德语文坛的最高荣誉。2006年3月18日,他参加了米洛舍维奇的葬礼。这再一次掀起轩然大波。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中被取消演出。“那么多人针对我,是大家都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左右,他们的报道是听从了一边倒的政治家的摆布,而民众对这件事情并没有一个非常独立的见解。”汉德克说,“西方主流媒体所操控的对作家进行的攻击一直就有,‘二战’之后实施的就有三个,针对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还有我。”
汉德克也不是反对一切标签,他说:“我自己是一个关于蘑菇知识的世界冠军,我认识所有的蘑菇品种。”“我是世界蘑菇大王。”这是他喜欢的头衔。2012年,他写作了《试论蘑菇痴儿》,里面讲述了一个痴迷于寻找蘑菇的人,一个因此失踪的人。这是他从1989的《试论疲倦》开始,以“试论”为题创作的第五部作品,此前还有《试论点唱机》《试论成功的日子》和《试论寂静之地》。这也是我们目前能读到的,由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韩瑞祥主编,世纪文景出版的9卷本汉德克作品集中,创作时间最近的一部,写于70岁之后的作品。
“试论”是一种法国传统的写作形式,最早蒙田也在这种形式下写作过。“我在法国生活了将近30年,所以从法国的文学作品当中接受了试论这样一种文体的写作。”汉德克说,在德语中,它类似散文,也是柏拉图曾经提出来的一种哲学的研究问题的方法。比如《试论疲倦》,就是在问自己“疲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就此来写一个论述。
因为人物和情节的存在,《试论蘑菇痴儿》在形式上更接近于一部中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和汉德克的经历有着很多相近之处,生长于同一个村庄、同样学习法律等等,因此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写作,被看作有关其人生的回顾和反思。作家承认这种自传性,至少对于蘑菇的痴迷,他就和主人公完全一致。
“这5篇试论可以看作一种断片式的对我人生的描写,都有个人的影子在里面。但是,你在里面不仅可以看到作家的影子,同时也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影子。”汉德克这样说,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在文中探寻到他的秘密,但也依然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单纯的寻找蘑菇的故事,仅仅体会那种对事物痴迷的力量和寻找的乐趣。毕竟,除此之外的汉德克现在的写作,我们知之甚少,而《试论蘑菇痴儿》也不过只是他“手指上的一片指甲”。
文学就是从最肮脏的媒介中寻找最纯洁的宝贝
——专访彼得·汉德克
“先锋”“反叛”“愤怒”“政治性”……对于彼得·汉德克来说,这些标签都不如“世界蘑菇大王”。
三联生活周刊:《试论蘑菇痴儿》是你被译成中文的作品中距离现在最近的一部创作,在这其中,主人公痴迷的“蘑菇”,就是蘑菇本身吗?有没有象征成分?
彼得·汉德克:没有任何象征意义,我关注的就是找蘑菇的这个过程。“一朵玫瑰花就是一朵玫瑰花”,对我来说,一个蘑菇就是一个蘑菇。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喜欢采蘑菇的人,我是世界蘑菇大王。我只收集野生的蘑菇,而不是人工养殖的,我关心的就是不能被养殖的这些蘑菇本身,这是大自然里面的物种。花、树、草都可以人工培养,一些蘑菇也可以,比如我们常在蘑菇汤里面吃到的那种,或者木耳等等,但是有一些野生蘑菇,有200~300个品种是完全无法由人工养殖的,我就是对这些感兴趣。我人生的第一笔钱就是10岁的时候把采来的蘑菇卖了,然后用那笔钱去买了书。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问是因为那篇文字里有很多自传性的因素,以至于“蘑菇痴儿”就像是你,或者说你的镜像。过去的几篇“试论”虽然也有你的影子,但是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人物形象出现。
彼得·汉德克:你的判断是对的。这5篇试论可以看作一种断片式的对我人生的描写,都有个人的影子在里面,《试论疲倦》《试论成功的日子》等等都是在讲我自己。但是,你在里面不仅可以看到作家的影子,同时也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影子,在不经意间找到对照。每一个读者看到《试论疲倦》时都会想到自己什么时候是疲倦的,会想到自己的身体感受。读《试论成功的日子》就会想到,对于你来说什么才是成功的美好的日子。《试论点唱机》,它在我的青少年的生活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意味着我能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而这个《试论蘑菇痴儿》,是讲你对一种事物的痴迷,开始可能只是热爱,然后慢慢变成一种痴迷,变成疯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人们一般把它当作散文,但其实它是一篇中篇小说,就像是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一样的中篇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几个试论里,谈到疲倦,讲到厕所,在人们固有的认识里,这些都不是有关美好的事物,但你都是从欣赏的角度,给它们赋予了新的意义。是有意反其道去打破固有的观念吗?
彼得·汉德克:可能厕所、疲倦会让人有不好的联想,或者形成一种固定的想法,我接受大家的想法,但是又想超越一般性的想法,关键还是想要叙述。比如《试论疲倦》,讲述疲倦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关于疲倦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感受,并不是想打破什么,打破惯例或者固有的思维都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去叙述,去讲述。
像是《试论寂静之地》,就是指厕所,你可能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在一个社交场所,你不停地听到别人说话,你也要不停地说话,但是突然在某一个时刻,你变得像自闭症患者一样不能说话,没有办法和别人交流。这个时候你本没有上厕所的需要,但是你会想要去厕所待一会儿,关上门,因为那是一片寂静之地。过一会儿,你缓缓地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出来了,你又能说话了,休整好之后从厕所出来,又可以重新社交。我从来没有想要打破传统或者打破规则,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更深入地去探讨的话题,疲倦,寂静之地,蘑菇的主题还是挺有意思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意思的是你让这种探讨带有一种研究性。
彼得·汉德克:其实这个可以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来欣赏,一方面是文学,一方面是研究,文学也应该有这种科研性。只有具备了研究的特性,才能称得上是一种娱乐,是一种文学。我说的这些话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作家的角度。我希望读到这样的文学作品,讨厌娱乐似的文学,那种就是为了让人分散一下注意力,放松心情的作品我非常不喜欢,文学是为了让人集中注意力去阅读的。但是当今的文学还是以娱乐性的为主,那些都不是文学,要是上帝在的话,就会把那些作家都赶出上帝的庙宇。佛也会这样做的,佛可能会拿笤帚把它们都扫出去。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娱乐性为主的文学,是否在某些方面就等同于你最近常提到的国际性文学?
彼得·汉德克:国际性文学就意味着你在哪里写作都是一样的,写出来的是一样的东西,无论是纽约、曼谷还是阿拉斯加,或者其他的地方。在歌德提倡的概念里,世界文学,说的是一个遥远的国家用文学向全世界展示什么是我的国家。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方式,每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你一看就知道是在写某一个国家或者城市,语言的节奏、描绘的画面都不一样,但是你同时会觉得它所描写的和你自己的某些感受是相通的。国际性文学是每个国家的文学作品都趋同,失去了本国的特点。现在的国际文学当中最不好的就是侦探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就写了那部没有主线、情节,但是有一些侦探元素的小说《推销员》?
彼得·汉德克:那是我的小说中,唯一一本让人读不太懂的作品,是一种对侦探小说的反讽。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奥地利文学和德国文学之间的差别主要在哪儿?
彼得·汉德克:每一个国家的文学都有各自不同的游戏方式,德国和奥地利的文学的游戏方式不同。奥地利作家的作品中常常有一些游戏的味道,而在德国作家的作品中,更加严肃,没有那么多游戏的成分,这可能是作家的性格不同。格里尔帕策就是非常典型的奥地利作家,他的作品和出生地之间有着很强的对应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框架里,你还强调了一个“精确性”的概念,怎么理解?
彼得·汉德克:我推崇那种不精确性。太过于精确就没有办法区分是不是亲身经历的。在文学当中,特别精确的时候你就会怀疑其真实性,它没有给读者留想象的空间。
我读老舍的作品时,读的是法语译本,译者翻译得不好,在很多描写的部分译者用的是典型的法国人的描写方式。他因此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将语言转换成一种法国人看惯的语言而破坏了世界文学,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一种灾难。在德国近来出版的很多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中你会发现,新的译本用了大家现在特别熟悉的语言,但是对比19世纪,德国人去翻译这些俄语作品的时候,语言非常真实,充分地带有陌生感,你会知道俄国人就是那样说话的,并且那些作品本来就是19世纪写的,也应该用相对应的19世纪的语言,保持古典的文风。现在的这种语言更具国际性,更为通行,但却等于失去了原汁原味,这种语言可能就更精确了,但就是这种精确可能会损坏原来的韵味。文学是一个大问题,但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令人愉悦的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文学。
三联生活周刊:语言的问题也是你在作品里讨论的,比如《卡斯帕》就寓意语言可以杀死一个人。语言不断更新,但始终都具有那种操纵性,你认为这种更新的意义在哪儿?
彼得·汉德克:太难描述这个感受了,语言是包容性最强的媒介,但是同时它也是最肮脏的一种媒介。语言是一把双刃剑,在和其他的媒介,图像、声音、音乐、绘画等等相比之下,是被使用最多的,也是最多被滥用的、最不纯粹的一种媒介,我们都在报纸、电视上见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辩证的问题。语言是最能包含纯粹性的,是可以对它进行净化的一种媒介,文学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将语言这种最肮脏的媒介转化为最纯粹的媒介,这就是从事文学的人所做的工作。
绘画、音乐,本身也是一种媒介,每次欣赏的时候,你都会意识到它作为媒介的存在,但语言的形式,让你意识不到,或者说忘记了它本身是一种载体。就好像你要读一首很美好的诗,并沉浸其中,并不会意识到语言其实是在作为媒介,只是体会诗的美好,所以文学就是从最肮脏的媒介中寻找最纯洁的宝贝。这是一个辩证法,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秘密。我更喜欢“秘密”这个词,超过“辩证法”。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总是在习惯性猜想你在写作中打破了什么,比如传统、规律、观念,就像是一个不断制造冒险的过程。你在写作中遭遇过什么真正的危险吗?
彼得·汉德克:每次都是,每天都会陷入危险。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来说什么是危险的?
彼得·汉德克:我是一个罪犯,我就像是一个被判了刑的人,我的身份是不合法的,我不属于人类。每天都在危险之中,也许这有点夸张,我是指每天都像流水一样过去,你会产生一种很无助的感觉,你会想说,“我想要获得什么呢”“我得到了什么呢”,陷入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危险。也许因为我是基督教徒,每天都会陷入对自己的原罪的追问,也许应该改信佛教,但如果成为佛教徒可能就成不了作家了。
(文 / 孙若茜)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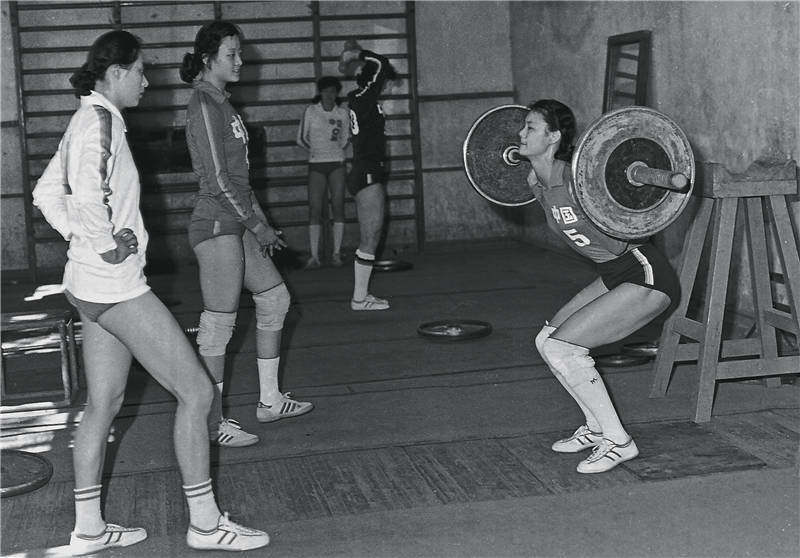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