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斯尧
2018年11月30日,安德拉斯·席夫时隔5年再次来到国家大剧院为观众献上一场分量极重的独奏会——从曲目的选择上便可见一斑:勃拉姆斯三部晚期钢琴小品集(作品117、118、119),“十分自然而平常地”穿插在莫扎特、舒曼、巴赫、贝多芬的作品中间。早在2016年秋天,趁他与北德广播爱乐乐团演出结束后预约他随后的独奏会时,大师半开玩笑地说:“未来的独奏会计划?你想要一场还是两场呢?” 想来,就已经为这场“雄伟”的曲目埋下了伏笔吧。

席夫先生于2018年11月29日晚9点落地首都国际机场,之后直接乘车来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挑选第二天的演出用琴。他20多年的好搭档、柏林爱乐的调音师托马斯先生全程陪伴。第二天上午,托马斯早早来到。音乐厅按照席夫前一晚的嘱托对钢琴进行了“脱胎换骨”的调整,之后席夫在舞台上用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把音乐会的曲目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排练过后,我们聊了聊有关音乐和演奏的事情。
张斯尧:您这次音乐会的曲目都够得上两场的量了。
席夫:我最开始想到的,是围绕勃拉姆斯晚期的作品讲好一个关于勃拉姆斯的故事。事实上我早先准备了两套曲目,今晚这套曲目脱胎于其中的第二套。我在今年整个巡演的过程中对曲目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后来除了勃拉姆斯之外,我觉得或许应该加一些别的作品,这样观众听起来会不那么费劲。所以我增加了一些其他作曲家的、大致上是同时期的作品,穿插在勃拉姆斯的这些作品之间,并尽量让整场音乐会在“调性”上保持连贯。
好比舒曼的变奏曲结束在降E大调,与勃拉姆斯作品117的第一首小品调性相同;莫扎特回旋曲是a小调,勃拉姆斯作品118的第一首也是a小调,它们相互关联着。下半场属于“3B”(巴赫、勃拉姆斯、贝多芬),勃拉姆斯处于中心,而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结束在降E大调,这可以看作是对整套曲目一开始演奏的舒曼作品在调性上的回归。
贝多芬这首奏鸣曲的标题“告别”,也正好合适放在整场音乐会的最后。其实不仅贝多芬这首第一乐章带标题的作品,舒曼的那首变奏曲也是他最后的作品。这样看来,不仅是音乐会的结束,也是一种向生活的告别;除此以外,这三首勃拉姆斯晚期的作品,对我而言,实际上也有很深刻的“告别”的体会蕴含其中。

张斯尧:如果观众看到曲目再结合您刚刚的解释,恐怕会担心您要告别演奏生涯了。
席夫:这不会。你知道贝多芬的这首奏鸣曲只有第一乐章是“告别”的标题,第四乐章寓意着回归,由很多标示为“积极地”的音符构成,所以这是一个幸福的结尾。此外这套曲目还有很多欢快的部分,并不总是弥漫着离愁。
张斯尧:在排练中我想我能找到这样一个逻辑:您用更富旋律性的舒曼、莫扎特来串联着上半场,并通过勃拉姆斯作品中的结构性推动着音乐的剧情;下半场也是一样的情形。甚至在听觉上,因为您在上、下半场进行不间断地演奏,所以这套曲目在演出过程中更像一个大的交响曲!您怎么保持演奏精力呢?
席夫:你说的没错,而我也一向乐于做这样的事——演奏这种大的曲目单。对演奏者来说,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心力的集中”:心理上的、情绪上的、脑力上的、身体机能等各个方面的统一与集中。这套曲目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安静的”、“内在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私密性的”,是作曲家写给自己的,而并不是那种辉煌的、炫技的、具有所谓“演奏效果”的。所以我讲的“集中”,不仅仅是对于演奏者在键盘前的操作而言,还针对你所要达到的演奏效果——你的演奏要能够让听众听得进去,让所有人都专注于这些“私人性的”的作品中,就好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家里一个人独自聆听那样。
张斯尧:现在蛮流行用一两个热点词、关键词来修饰和概括作曲家的。
席夫:很显然我们不能仅用所谓的“关键词”来概括那些伟大的作曲家,每一个人都太难以解释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只顺着一个线索去分析作品,每一部作品都是不同的。就拿贝多芬来说,他的作品不都是愤怒的。有戏剧性的作品,有旋律优美的作品,当然还有诙谐有趣的以及带有幽默感的作品。
或许对于听者而言,“旋律”总是比较容易辨识的。但是别忘了旋律只是作品特质的一个层面,你还需要留意“和声”。所以,我们至少需要从横向的旋律与纵向的和声这两个要素来考虑一部作品。最终能够把横向、纵向两个方面结合到一起的要素是——节奏。节奏对于一部作品真是难以想象的重要。此外还有体裁、曲式、结构等要素需要考虑。
有意思的是,刚刚提到的这些因素都是可以被分析的;显然,音乐作品中还有那些无法分析的东西。比如:“表情”或是某些“音乐的特质”等难以言表的、但对于演奏者来说却更为重要和难以掌握的内容。当所有的这一切相互交织,并通过演奏者准确的诠释传递出去时,观众一下就能知道,这是一首戏剧冲突明显的作品、还是一首具有内在张力的作品,要么是一首抒情的小曲、亦或是幽默的片段。

张斯尧:您知道,当很多人知道的和您一样多时,他们一定会弹出“懂很多事情”的样子。但是当您弹琴的时候似乎可以把这一切抛在脑后,纯粹地弹属于自己的风格。
席夫:哦,你知道,我从来也没有刻意地要去实现“我的风格”。我一直想要做的是呈现作曲家希望我做到的事情。是的,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我事先调整钢琴音色的做法不太常见,但那是这些作品“告诉”我应该这么做的。
张斯尧:来说说这场音乐会的“声音”吧,和常规相比,似乎这次钢琴的声音要“暗淡”很多。
席夫:是的。因为我需要钢琴的音色与音乐一致,所以才会根据不同的作品来调整钢琴——我总觉得勃拉姆斯晚期的音乐有一种暗淡的特质,想想看,那种暗的色调和背景,而不是明亮的颜色。所以我让托马斯(本场演出的调音师)做了相应的处理。
张斯尧:所以您会首先根据不同的作品来调整钢琴让其达到不同的声音状态?
席夫:是的,这是最先要做的工作。当然在达到这个境界前,你首先要能在同一台钢琴上找到属于每一位作曲家不同时期作品的声音特质。贝多芬可以陪伴演奏者的一生,巴赫也是如此,乃至“早于”贝多芬。在巴赫之后,贝多芬以他无比博大的胸怀,在他那些伟大的作品中探讨着音乐之外的内容——那些关乎全人类的命题。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类比:比如肖邦就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但你在肖邦的作品里就很难看到贝多芬所思考的宏大命题——这些音乐之外的内容是关于贝多芬的普遍性的讨论,源自作曲家的独特经历。我每次演奏贝多芬都会“发现”新的细节并从中获取心得。再说到巴赫,很显然,巴赫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张斯尧:尽管您此次的曲目单里只包含一首巴赫的作品,但既然说到这儿了,看上去对于巴赫,一部分演奏者会卡在“声部独立”这个问题上,有时甚至把这当作练习巴赫的唯一追求。
席夫:很显然,除此之外还有好多事情需要做呢,比如声音的倾向。但是我想,对于演奏巴赫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正确体会他的精神与信仰,去相信他所相信的。巴赫是信上帝的,尽管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信仰,但当你在弹巴赫的作品时,你或许可以试着让自己沉浸在他的信仰里,因为他的音乐是关乎他的信仰的。
张斯尧:在大多数的教学中学习巴赫的步骤是:小步舞曲-二部创意曲-三部创意曲-法国组曲-英国组曲-平均律键盘曲集。
席夫: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顺序。你知道巴赫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不同程度的作品,让我们可以比了解其他作曲家更容易,亦或使我们能够更早地接触他的作品,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他有很多孩子同时也处于不同的学习程度。所以这么看来,巴赫首先也是个很好的音乐教师,他会思考有关音乐教育的问题。他为自己的孩子们创作的例如《小前奏曲》《二部创意曲》等初级作品,就很适合我们在最初接触巴赫时演奏。而且即便从《二部创意曲》这类所谓的初级作品中,你都可以学习到巴赫在那些伟大的作品中所运用到的复调写作手法,你应可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学习如何演奏对位的声部进行,如何使你的演奏呈现两个独立的声部,之后才是三个声部。这种演进的过程非常重要。
我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十来岁的小朋友在老师的要求下生硬地弹奏《哥德堡变奏曲》,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样的演奏。对于演奏《哥德堡变奏曲》来说他们太年轻了,他们没有做好弹奏这样作品的准备。或许他们在“手指弹奏”上很有天分,但他们还需要时间,要给他们时间去一点一滴地积累。这就是我给出的建议——而这对于演奏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也是同样适用的。
你总不能让一个孩子去演奏贝多芬晚期的作品吧。不仅因为贝多芬在写下这些晚期作品的时候已经是位老人了,还因为贝多芬作为一位天才的作曲家,其艺术创作上的成长速度超过常人。我们作为普通人自然要通过生活而经历“自己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免不了要去克服不少困难,有时甚至要走些弯路,才能慢慢积累、慢慢接近贝多芬的精神境界。有些年轻人或许能弹得很熟、很快,能“弹奏得很好”。但很遗憾,事实上他们还没有能够领悟到这些作品的意义、情感、深度以及所包含的大量信息。演奏需要时间,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这一点是难以跨越的。

张斯尧:我们听到一些演奏者在弹奏“平均律”时,把“强调主题”作为重点进行练习。
席夫:主题只是“平均律”中的一部分,它和答题、对题、连接段等其他的部分一样,没有谁比谁更重要这一说法。这与19世纪浪漫主义那些由主旋律及伴奏组成的作品完全不一样——巴赫的作品中也不存在这一现象。所以对于巴赫作品中的主题,你需要知道它、留意它,此外你还需要注意到它之后怎么样了,比如在各个声部中的发展、倒影以及装饰等变化。作为演奏者,你必须能够听到一首赋格中所有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听到了主题。
张斯尧: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你想要听到所有的内容,你就不能刻意强调某一个内容?所以对于演奏者来说,“平衡”就显得很重要?
席夫:完全正确。并且对于“平衡”的理解是很重要的。当你在演奏现代钢琴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层次,用不同的音色处理不同声部中的材料——这点在羽管键琴(harpsichord)上就没法做出来。反之,在羽管键琴上,你其实没法像我们现在以为的那样去通过音量大小来强调主题,羽管键琴每个音的力道是一样的——而这其实才是存在于巴赫脑子里的声响效果。
很显然他并没有弹过像施坦威这类的现代钢琴,也不曾想过像我们这样在现代钢琴上去处理各个声部。他倒是试过一些改进过的早期键盘乐器,羽管键琴只是他用来创作键盘乐作品的一种乐器,他最喜欢的键盘乐器还是楔槌键琴(Clavicord)。在楔槌键琴上,你是能够做出一些细微的、与我们今天能做的力度变化类似的声音的变化。尽管这种乐器的音量很小,但从音乐上来说它是件完美的乐器,我刚刚用楔槌键琴录完一张唱片。用它能触及到音乐中那种平静,真是很难以置信。我希望能通过多做这样的事引发听众对于这类问题的思考。有机会你也要弹弹看。我自己家里就有一台,时不时弹一弹,是个挺好的体验,你还可以自己调整不同的音律试试。

张斯尧:您让我想起一位今年夏天来过的钢琴家——柳比莫夫(Lubimov)。他就极力坚持用相应的乐器弹奏早期作品。
席夫:柳比莫夫也弹现代钢琴。当然,反过来说,我也喜欢用早期键盘乐器演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了解比如海顿、莫扎特、舒伯特时期的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的。我在博物馆、在收藏者的家里弹不同时期的乐器,来收获尽可能多的音乐的信息,之后我就可以用这些音乐的信息指导我在现代钢琴上的演奏。这个方法不光对于早期作曲家的作品,对于勃拉姆斯也是一样。我们甚至可以知道,勃拉姆斯有过什么型号的钢琴,演奏过什么钢琴,比如贝森朵夫、布鲁特纳等等。你会发现当时这些乐器有着现代钢琴的雏形。
张斯尧:对于很多人来说,用现代钢琴弹奏早期作品会被很多具体的问题困扰,比如音量啊、踏板啊、速度啊等等。你是怎么达到一个自如的境界的?
席夫:我掌握这些音乐的信息!在现代钢琴上演奏早期的作品,你必须要经历一种“重新的思考”。因为相比之下,贝多芬时代、舒伯特时代、勃拉姆斯时代的“钢琴”的音域是不一样的。现代钢琴有着从低到高的广阔的音域。我们也很容易就能做出一个“重低音”的效果。
有时候,我想让低音听得清楚一些,这时就需要把思路拉回到早期乐器上去重新思考。因为我听到太多的演奏者把低音弹得太重了,以至于把它上面的音全都盖住。要知道,这可不是在弹改编曲。是的,现代钢琴有自身的声响特质,但演奏者应该先去了解和熟悉那些作品在原来的乐器上的声音,从而获得更多音乐的信息,这样他们就不会认为用如此厚重的低音是合理的了。更有甚者肆意地制造出更大的音量,那简直就是噪音。
张斯尧:我们似乎谈论到了演奏者的角色问题。
席夫:对我而言,要知道我不是作曲家,我为音乐服务,我是作品与听众之间的信使,要将音乐的信息传递给倾听它的人。很明显,我不能否认,我自己的个性或我个人的见解有时也将成为我所诠释的音乐的一部分,就像每一个演奏者所做那样。这样的诠释因人而异,甚至我自己每一次的诠释也不尽相同。就好像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哪两天是相同的。
但是,我自己的个性绝对要在尊重作曲家想要表达内容的前提之下。就好比在演奏巴赫的作品时,你拥有大量的自由选择——他在谱面上标注的指示实在是少之又少。我这次演奏曲目中的前奏曲与赋格倒是个例外。他给前奏曲标注“行板”(Andante),给之后的赋格标注“广板”(Largo),这真是很少见的——即便如此,你选择什么速度,什么力度,你仍然可以有很多自由的处理。之后对于莫扎特,我想这样的自由度会少一些,对于贝多芬又会更少一些,他们开始在谱面上写出明确的指示,更不要说再往后的舒伯特、肖邦等等。你需要遵循作曲家的意图,比如你不能在贝多芬写了“突弱”的地方还一直保持着“强奏”,或对标记了“突强”的地方熟视无睹。还有,当作曲家标记了“反复记号”希望作品中的某一段落需要“反复”弹奏时,你更没有权利不演奏“反复”,因为作曲家已经写了!
所以对于演奏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想清楚自己的“自由”和“责任”是什么。如果你觉得舒伯特最后一首奏鸣曲按谱面标记的“反复”演奏太长了,那你干脆就不要弹这首作品,而不是弹一个不加反复的版本,我真的不赞成这种做法。
张斯尧:在大多数考试中,“反复”都被无情地叫停了。
席夫:哦,在考试中啊,这个情况就比较特殊了(神秘的一笑)。但在音乐会中,演奏者为什么不弹反复的部分呢?难道是没有耐心了,或是赶时间吗?
张斯尧:您觉得“反复”的意义是什么呢?
席夫:反复意味着不同,意味着变化。很多时候你需要想象一首奏鸣曲在它第一次被演奏的时候,对于观众来讲它是一部全新的作品。音乐的“反复”给了听众第二次机会去欣赏与熟悉这些段落,此外,有些“反复”的段落还涉及作品曲式结构上的功能,比如古典奏鸣曲通常在呈示部进行“反复”,后接展开部和再现部,就能让作品更加平衡。如果你不演奏“反复”,从整体上看就失去了这种平衡,古典作品所特有的结构美感也就荡然无存。
张斯尧:没有音乐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席夫:不可想象。我喜欢很多事,阅读、旅行、散步等等。每件事都是相关联的。我每次会保持注意力的集中,练琴2-3个小时,从不浪费任何时间;不是机械地练习,有时我会把曲目过一遍,但不是用演奏的速度或力度,但在脑力上是全力以赴地对音乐进行思考。
张斯尧:能与您聊聊音乐真是个很愉悦的过程。但我们也都知道还有一种“情况”,大家更习惯称之为弹琴干活挣钱。
席夫:是的,从古至今都有这种情况,真是很不幸。他们(作为演奏者)应该为此感到羞愧。音乐不是打工,不是娱乐,音乐是被赐的恩典。它鼓舞、启发人的心智,让我们变得更好。但如果你只是把音乐用作娱乐,你就背叛了音乐,我们真的不应该low到如此地步。
音乐会侧记
至今记得,早在去年夏天收到经纪公司发来的邮件里看到这套曲目的那一刻,我内心是犹豫的。毕竟,无论是勃拉姆斯的三套小品集、还是“周边的”部分——舒曼的变奏曲、莫扎特的回旋曲、巴赫的平均律和贝多芬的“告别”钢琴奏鸣曲,单拎出来都可以单独撑起一场小型的音乐会了。于是,我专门把作品集的小标题补在邮件里发回给对方,并最终得到这样一句有趣的确认:“尽管我们也不太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师这次就想这么弹。”为此我期待了将近一年,这自然也是工作中的一种乐趣。
从选琴、排练,到最后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自己的表演,席夫大师始终展现出一种温文尔雅的古典风范,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从容。有时我和他开玩笑:“您还用练琴啊,感觉没啥您不能弹的了。”大师也会很幽默的说:“我得练啊,我得保持。而且老了以后啊,我更喜欢练了,就像生活中的必备内容,不练琴我真的不舒服。”
与此同时,还有个细节不得不提。本次音乐会全部的调律工作都是由与席夫搭档了20多年的调律师托马斯完成的。这次见面寒暄时,我与他提到,上次来的时候他带了个“小惊喜”——一个可以插在钢琴盖支架前段的“神器”,以达到让琴盖获得更大开合角度的目的。“这次我带来的惊喜更大!”他指了指背后。我才注意到这次他带来的是一整根支架,比普通的三角琴支架更长。之后托马斯极其熟练地把它替换到钢琴上。“上次那个小玩意儿容易产生杂音,这次这个好,稳定。”说完,托马斯还拿出一些木塞垫在琴盖折叠处。“这样就完全安静了。”德国人注重细节的品性展露无遗。
音乐会最终比我们期待的更精彩。要知道,把曲目列出来是一回事,而能真正将它们演出来是另一回事,其中涉及的不仅是将每一首作品完成好,还需要艺术的直觉和智慧来进行整体的谋篇布局。加上足足7首返场曲,也就难怪这场演出被很多乐迷开玩笑地称作是“提前预定”全年最佳独奏会。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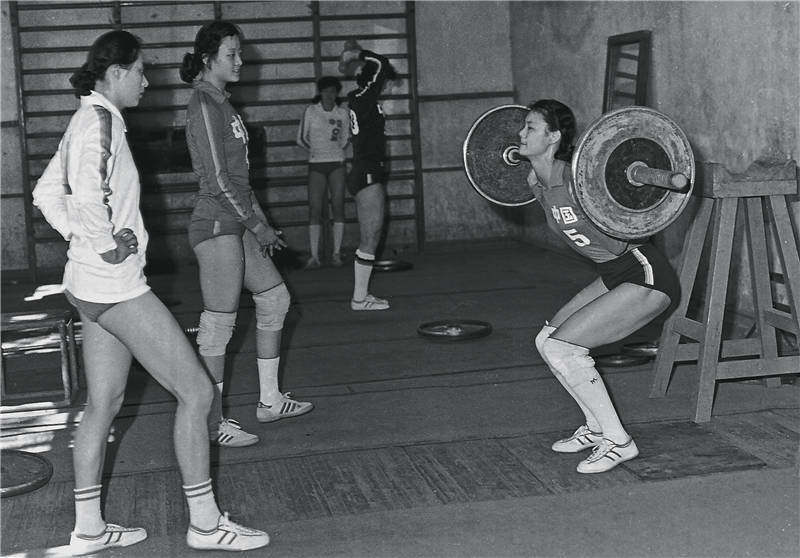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