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姚建龙(金海 摄)
大连13岁少年杀人,因未满14岁,无法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引得舆论一片哗然。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姚建龙看到的,却是不同社会对少年观念的差异。作为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上海市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他向我们讲述,面对屡屡发生的少年极端恶性事件,司法应如何坚持自身的正义。
少年法的意图
三联生活周刊:大连13岁少年杀人事件发生后,作案人因年龄未满14岁,无法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目前的处理办法是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舆论对此一片哗然,认为法律没有实现正义。从专业角度看,对于类似的少年犯罪的极端事件,司法界关注的是否同样是刑罚的问题?
姚建龙:类似的极端案件在各国都有,日本有两个案例最为典型,可以作为对人们面对类似案件的反思。
其中一个案例是“酒鬼蔷薇圣斗事件”,也是未成年人杀害未成年人,但性质比大连杀人案要恶劣得多。1997年,一名日本神户市的14岁学生在3月至5月间,分别杀害了一名11岁男童和一名10岁女童,其中杀害男童的行为尤其残忍。
少年的暴行在当时的日本引起全民的恐慌,当时日本的犯罪刑责的最低适用年龄是16岁,也就是说,这个少年不可能受到刑罚处罚。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对该少年的处理方式。不能适用刑罚是否就“一放了之”呢?
少年被逮捕后,依据日本的《少年法》,他的信息被完全保护起来,只以“少年A”作为称呼。少年法院发现少年A的家庭存在问题,少年A的母亲给他施加很大的压力,强迫他在学校表现突出。即使社工提醒这位母亲,少年的精神状态不稳定,在当时已经把虐待和杀害小动物当作“嗜好”。最终神户家庭裁判所判定将他送入有医疗性质的“关东少年感化所”诊疗,之后又将他送到次一等的“东北中等少年院”。2004年已经成年的他获得全新的名字和身份,重新进入社会,没有再犯罪。他之后还主动出书,记录自己曾经的经历。
这个案件说明,即便面对恶性少年,少年司法的首要原则不是报应,不是“一罚了之”,而是“以教代刑”,也就是“宽容但不纵容”。有人可能会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表达极大的不满,罪行如此恶劣竟然没有受到刑罚处罚,更没有“杀之而后快”!的确如此,在当时的日本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这个案件,2000年时日本修改《少年法》将可以适用刑事处分的年龄调低到了14岁,这也被中国的一些学者解读为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但是,这一法律的修改一直饱受争议,事实上迄今也没有真正适用过。更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少年A被判处重刑而不是留在少年司法体系中教育矫治,他是否仍然可以顺利回归社会?
日本的《少年法》于1922年颁布,在1948年进行了大幅度修改,是一部完全独立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少年司法拥有特殊理念、特殊立法、特殊机构、特殊程序、特殊处理措施。简而言之,它着力淡化“罪”的概念,在中国被视为未成年人的犯罪、违法事件,在日本被称为“非行”,它的目的不是报应,而是保护。与家庭法院配套的是系统的保护处分措施,以及各级少年院。少年院不是监狱,更像一个学校和医院。少年犯再大的罪,首先考虑的仍然是“保护处分”而不是“刑罚”。
另一个案件是更为知名的“福田孝行杀人案”,这个案例能够说明当作案人的性质过于恶劣时,如何在法律框架内实现惩罚、报应的目的。
1999年4月14日日本山口县光市,18岁的少年福田孝行闯入民宅,企图强奸23岁女屋主未果后,先将女屋主杀害奸尸,又将爬过来的婴儿活活摔死。日本的成年标准是20岁,而福田孝行最终被判死刑,似乎成为一个重判“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但实际上,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8岁以下不得判处死刑,这是全世界认可的底线,福田孝行当时已经年满18岁,并没有触碰这条底线。
他能够判处死刑,最首要的一点是因为行为过于恶劣,负责审理14岁至20岁少年非行事件的日本家事法院放弃了管辖权,把这个少年剔除出了少年司法体系,由检察官“逆送”交给了普通刑事法院当作成年人案件来审理,由此才可以适用普通刑法,适用刑罚处罚。这在法理上也被称为“恶意补足年龄”,即未成年人做出犯罪行为的时候,如果主观恶性程度极高,则可以剥夺“未成年人”身份,当作成年人由普通刑事司法体系而非少年司法体系来处理。
进入成人法院后,起初福田孝行被判处的是无期徒刑,他被判处死刑的结果也值得玩味。他被判处死刑有两个关键背景:一个是当时被害人的保护工作普遍欠佳,在审判和案件报道过程中,被害人的照片被披露,案情被详细地描述,被害人家属受到伤害,被害人家属向天皇请愿,发表演讲,掀起被害人保护运动,民意汹涌,连当时的首相都明确表态支持被害人。同时,确认他悔罪的关键证据改变,他甚至称受害人为“母狗”,由此被改判死刑。而到目前为止,不仅福田孝行仍关押在广岛的看守所,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律师团自愿站出来,希望改判,他们反对因为一个极端案例,就轻易判处少年死刑。很有可能的结果是,福田孝行虽然被判处了死刑,但是实际执行的可能性很低。
从这个案件可见,少年司法也不是只讲保护,对于个别极端恶性的少年,也会动用刑法,给予刑罚处罚。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他国际公约,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严禁判处死刑,也不得判处无释放可能的终身监禁,全世界都是这样。也就是说,不可能把未成年凶手杀掉,即便将少年关进监狱,他们也总归会被放出来,如何保证那时的他不会变本加厉地再犯罪?因此,又回到了教育、矫治这个问题上。现在我国关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降低的争论,特别是那些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还只是“欲罚之而后快”,实际还没有想到这一层。如果刑罚能解决犯罪问题,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犯罪了。
司法具有保守性特征,刑事责任年龄是否降低关系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根基,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不可不慎。少年司法从刑事司法中独立出来,对未成年人罪错甚至是严重的罪行仍然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处理方式,仍然强调“以教代刑”而不是刑罚处罚,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对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争议背后,更是如何看待儿童观念的冲突。

(插图 老牛)
“少年”概念与司法
三联生活周刊:看起来,注重教育和矫治而非惩罚的背后,是“少年”独立于成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姚建龙:现代“儿童”概念的形成距今不过二三百年。在18世纪之前,主流社会要不把孩子看成是“小大人”,要不将他们视为成人的所有物或附属品。他们一旦能够行走和说话,就加入成人社会,穿同样的衣服,玩同样的游戏,完成同样的工作。甚至当时的科学家也大多秉持胚胎学的“预成论”,相信一个极小的、完全成形的小人在怀孕时就被植入精子或卵子之中,人在被创造的一瞬间就形成了,直到诞生时不过是身体长大了而已。即使没有直接证据,也会争辩说是由于那个小人是透明的而且小得看不见罢了。
但“预成论”大行其道的同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认为“人生而平等”,儿童生下来既不善也不恶,是一块“白板”,由此将少年犯罪和不良行为引向后天的环境和教育。随着启蒙运动的推动,从17世纪开始,“童年”(Childhood)的概念随着资本主义的勃兴而发展,有产阶级家庭视儿童为“可爱而值得宠爱的”,开始依照儿童成长的各阶段需求,制作专门的服装、玩具和游戏;同时清教徒教士和道德教育家提倡,因为儿童的心灵易受到迷惑,要对儿童施以道德管教,使心灵脆弱的儿童得到保护,并获得矫治。由此卫生保健机制和学校教育制度被确立起来。在18世纪时,“童年”的概念和与成人独立的“儿童”“少年”概念被确立起来,并且根据成长阶段的不同需求,分为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儿童时期重养护,少年时期重教保。
与之相应的司法概念也独立出来。19世纪初,欧美国家出现“少年罪错”(Juvenile Delinquency)的术语,替代罪行(Crime)的概念。比如1817年在纽约防止贫困协会的调查报告中,美国首次公开使用了“少年罪错”一词,意指犯法、怠学怠业在街头游荡,或欠缺正常家庭的不满21岁的人。
而在现代司法中,各国规定少年的刑事责任年龄有大有小。根据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标准是“根据孩子本人的辨别和理解能力,决定其是否能对本质上反社会的行为负责”。截至2019年,世界上共有主权国家195个,梳理发现,各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最低的为0岁,最高的有18岁,但规定最集中的刑事责任年龄是14岁,其背后是严谨的脑神经科学成果。科学家们发现,像前额叶这样进行决策和情绪管理活动的大脑分区发展最晚,到青春期结束才能成熟。所以虽然少年具备了一定的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但不能像成人一样严格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人类在14岁左右进入青春期后,大脑结构重塑,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对威胁、奖励的感知也与成人不同。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死刑不能低于18岁。而科学研究表明,人类要到25岁时前额叶的发育才完全成熟。在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法学家们便依此建议,适用少年司法的年龄应延伸到25岁,要考虑特殊的保护规则。
三联生活周刊:与之配套的少年司法又是如何形成的?
姚建龙:美国是少年司法的发源地。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前期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当时的美国社会结构经历了一个重组过程,大量欧洲和亚洲移民涌入,城市人口急剧扩张,农业经济快速向工业经济转变。
儿童与在工厂做工的父母一同来到城市,贫困和“童工”的问题凸显出来,少年犯的问题也随之增多。19世纪初在美国兴起“拯救儿童”的运动,为少年建立庇护所和少年教养学校等少年矫正机构,收容流浪或小偷小摸、逃离济贫院等轻微违法行为的孩子。但这些矫正机构大多蜕变为监狱或能够合法使用童工的地方,手铐、脚镣、鞭打的管教方式很普遍。而犯罪的少年与成年人在相同的刑事法庭审判,与成年罪犯关押在同样的监狱里,甚至发生过七八岁的孩子与成人关在同一个监狱,搬咖啡桶的时候,掉进去被烫死的惨剧。
当时以珍妮·亚当斯、露西·弗劳尔等一些州长女儿、妻子为代表的女性精英,不忍心看到这种情况发生,致力于拯救儿童运动,要为儿童建立一个更人道的法律制度。1899年的7月1日,在少年矫正机构改革的基础上,伊利诺伊州终于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少年法院法》,并在库克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少年法院。少年法院成立之后,很快形成了席卷全球的少年法院运动,日本曾经的少年法院和现在的家庭法院也是它的余绪。
各国具体的少年司法制度有所差异,核心的理念却是共通的。人们奉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将少年罪错现象视为“越轨”行为,归结为国家和家庭对少年教育不到位,甚至疏忽、虐待的结果。少年司法干预的目的是为少年谋福利,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使其得到康复,而非惩罚他们。1989年联合国颁布的《儿童权利公约》的内在精神也与此有关。
在此理念下,少年司法不但在架构上,在术语上也与刑事司法完全分离。在少年法限定年龄下的少年,没有触犯法律,但无人抚养或被忽视,也会得到关注,而不论少年触犯法律的行为是什么,统一被视为“罪错”,均由专门的少年审判机构管辖。审判场所、人员和拘留场所都与成人法庭分开,为罪错少年安排独立的教养机构。少年司法在原则上更为弹性和私密,少年需单独审判,判决摘要、记录也需单独制作。而且,触犯法律的少年不再被称为“罪犯”,而称为罪错少年(Delinquent),审理少年案件也不称“控诉”而称“呈请”(Petition),有罪处理的结果不称“判决”(Sentence),则称“处置”(Disposition)。
尤为重要的是,为实现少年司法的康复目的,确立了观护制度与之配套。比如伊利诺伊州的《少年法院法》第6条就规定,少年法院有权委任名声良好、行为谨慎的人做罪错少年的观护人,观护人需要对孩子进行调查、代表孩子利益出庭、根据法官要求向法院提供情况和帮助、按照法院指示在审理前后照料孩子。观护人的工作在当时是志愿性的、无偿的,而后来则逐步演变成为有偿性服务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工作。

2009年3月19日,在北京海淀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2009年工作会上,来自公、检、法、司和教育系统的专家汇聚一堂,观看了现场模拟法庭案例演示(andy /视觉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框架下,司法如何回应随着社会发展,少年生长变化的状况,比如“早熟”的问题?
姚建龙: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确实有许多学者认为少年有成人化的趋势,他们认为少年与成人之间的差距在重新缩小,依据是他们把文字当作少年与成人的分野,儿童学习文字、了解信息的过程就是少年的阶段。而在网络时代,一个7岁到10岁左右,具备自主活动能力和对音像图像具备基本识别能力的儿童,就能够知晓成人世界的一切秘密,儿童与成人的分界线变得模糊。生理科学也显示,欧美女孩的发身期一直在提前,女孩的月经初潮时间由1840年的17岁左右,到上世纪80年代时,已经降至低于12岁,而男孩发身期比女孩晚两年,也在提前之中。
降低少年刑事责任的年龄与此有一定关联,不过各个国家的少年刑事责任年龄整体来看有升有降,原因也不与少年成长直接相关。像“酒鬼蔷薇圣斗事件”,就是因为一个极端事件,刑事责任年龄被调低。但在2004年日本又出现一起11岁少女杀人事件后,日本社会反思之前调低年龄是否过于草率。而因为有《少年法》的制度作为缓冲,即使调低刑事责任年龄,家庭法院仍首先会做审查,极少有放弃管辖权的情况,调低刑事责任年龄对实际的司法影响不大,也不是法律界所着重考虑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就我国而言,若调低刑事责任年龄,效果是否相同?
姚建龙:大不一样。因为我国没有独立少年司法制度,未成年人犯罪只是比照成年人从宽处罚。调低刑事责任年龄就意味着直接用《刑法》来惩罚年龄更小的孩子。看待像大连杀人案这样的极端案件,不在于它的性质有多严重,而在于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背后,所反映的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发展程度。呼吁调低刑事责任年龄背后,仍是把儿童当作“小大人”的落后观念,实际是把孩子的行为当作“恶”,并主张用惩罚的方法“以恶制恶”。
实际上,中国现在的情况与美国的“进步时代”非常类似,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就像美国那时的童工问题,而美国曾在此基础上催生出保护少年的法律。在我看来,“早熟”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从中国立法的历史上来看,清末《大清新刑律》中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12岁,可按照少年“早熟”就应该降低年龄的逻辑,清朝时的刑事责任年龄应该设得很高才对,结果恰恰相反。
中国现行《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14岁年龄的设置有其客观依据,也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沈家本在主持中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时,参考当时各国的法律和中国“丁年”的历史传统,本想将刑事责任最低年龄定到16岁,但因当时的国情,受到一致反对,最终定到了12岁。
刑事责任年龄的提高,意味着社会对儿童作为独立于成年人的存在的认知的提高。沈家本当时想,即使那时定得低,未来也会达到与世界先进国家相同的水平。后来也正如他所期望的,1928年的民国旧《刑法》,把12岁提高到了13岁,1935年的民国新《刑法》,提高到了14周岁。新中国成立之后,1979年的《刑法》也定在了14周岁,与当时初中毕业生走入社会工作的情况差不多。同时又规定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只对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1997年修改《刑法》时,又对严重犯罪的范围进行了限定,防止这一条被滥用。经过了约100年,终于快接近实现沈家本的理想了。
就我所知,尽管媒体报道的极端个案时常影响深远,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目前低于14岁儿童的恶性犯罪情况严重且普遍,14岁的年龄是历史演变的结果,更符合现代脑科学的研究结论,也与主权国家最常见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一致。若因为极端个案所引发的汹涌澎湃的质疑和公众的怒火,便擅自修改刑事责任年龄,恐有草率之嫌。不管怎么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都会面临更低年龄儿童犯罪问题——除非取消刑事责任年龄。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完善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体系,也就是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
成人社会对于孩子的成长负有直接的责任,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不能仅仅归责于儿童,还要考虑监护人、学校、社会的责任。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角度看,现在的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儿童,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又不能工作,甚至不允许抽烟、饮酒、夜不归宿。法律既然没有给予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样的权利和自由,就不能让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承担一样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
最重要的是,调低刑事责任年龄“牵一发而动全身”,未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保护始终连在一起,它不仅涉及可能犯罪的孩子,也会涉及受害的孩子。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会动摇对未满14周岁儿童,特别是幼女进行特别保护的法律根基和公众观念。当前性侵幼女现象日趋严重,法律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对未满14周岁幼女的保护,而不是动摇14周岁这个年龄底线。

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丰盈制衣劳模扶贫工厂内,女工在缝制服装,孩子们在一旁认真写作业(王威 摄 /视觉中国)
“一放了之”与“一罚了之”
三联生活周刊:公众的哗然似乎也在于收容教养并不能达到矫治的效果,《刑法》第17条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收容教养的具体场所,乃至采取的措施,都没有明确的说明。
姚建龙:确实如此。在现行法律,特别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刑法不做重大修改的情况下,在理论上收容教养是矫治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低龄未成年人的措施,也是被寄予厚望的措施,但这是收容教养“不能承受之重”。
收容教养实际上是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按照国际惯例和基本法理,未经法院审判,不能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错少年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就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养,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这也是收容教养制度被称为“小劳教”而备受诟病之处。雪上加霜的是,2013年劳动教养废止后,收容教养没有了合法的执行场所,不得不需要收容教养的孩子,基本被放入未成年犯管教所,甚至其他成年人监狱执行。未构成刑事犯罪的少年放在了刑罚执行场所执行收容教养,这显然是违法的。
我曾到一个未成年犯管教所调研,一个孩子以为我是领导,拉着我的手说,他跟另外几个未成年人共同干了一件坏事。主犯判了三年,他因为年龄没达到14岁,警方决定对他收容教养两年。结果,他发现自己虽然没有构成犯罪,但却也与主犯一样,被关进了未成年犯管教所。更糟糕的是,主犯因为表现非常好减刑提前走了,他因为不构成犯罪只是被收容教养,不能“减刑”,仍然被关在里面,实际比主犯待在未成年犯管教所的时间还长。另一个小插曲是,这个未成年犯管教所的所长向我咨询,他只有刑满释放通知书,这个小孩还有几个月就要放出去,但他不知用什么文书来处理。类似的尴尬,恰恰能够说明我国少年司法体系目前的漏洞。
中国未成年人专门法典最重要的有两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前者滥觞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中国社会转型,社会治安问题较严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严重化引起关注与担忧。1987年上海颁布《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成为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性法规。在此基础上,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颁布,将年龄界限清晰的“未成年人”而非年龄界限模糊的“青少年”作为法律名称,初步确立“未成年人法”这一专门的法律类型。但《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后,未成年人犯罪下降的比重并没有符合立法者的预期,于是国家又在1999年颁布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专门立法的思路是把青少年违法犯罪看作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利所致,对犯罪强调事前预防,并认为青少年犯罪应该综合治理。这个思路没有为少年司法的立法留出空间。虽然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但从适用的法律、诉讼的程序就可以看出,它仍然属于成人司法。甚至少年法庭的生死存亡一直是一个严峻问题,政策变化、领导变更都常常会给少年法庭带来“灭顶之灾”。
这两部法律也一直是没有“牙齿”的,被归入“社会法”的范畴,不会在公检法处理案件时引用,不具有“司法法”的特征。处理中国少年罪错案件的依据同样是针对成人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中国司法中没有“少年罪错”的概念,其内涵被《刑法》中对犯罪行为的规定,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分担。现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不良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份不良行为,比如抽烟、喝酒、夜不归宿;另一类是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等轻微违反治安行政法的行为。“严重不良行为”也分为两类,一类是类似多次偷窃、参与赌博、屡教不改等严重违反治安行政法的行为;一类则是触犯法律,却因为不满16周岁而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这样的分类虽然体现了分级干预的思想,但存在不同性质的行为跨度太大,且行为边界不清晰等问题。
判处监禁刑的未成年犯专门羁押在未成年人犯罪管教所。虽然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专章,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仍没有脱离成人的刑事诉讼程序框架,仅通过法律援助、法定代理人及合适成年人到场、分押分管、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等特殊程序,使诉讼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涉罪少年的特点,少年最终仍要与成人一样面对刑罚的处罚。我把它称为“逗鼠困局”,温情脉脉的少年检察官与少年法官,在走完一系列特别为少年设计的程序后,将同样适用成年人的刑罚加诸少年,这种做法与小猫逗完捕获的小老鼠后一口吃掉异曲同工。
在“严重不良行为”一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5条第2款规定:“对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但因缺乏完善的保护处分制度设计,难以及时有效的干预,中国的少年司法面临着“养大了再打”“养肥了再杀”的“养猪困局”。
如今的专门学校曾被称为工读学校,最初创立于1955年,以满足用教育手段容纳和矫治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上的大批孤儿及流浪少年的需求,受苏联高尔基工学团的影响,采用“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经过“文革”十年的中断,改革开放后,我国犯罪率飙升,青少年犯罪率在那个时代特别突出,工读学校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当时工读学校的招生由公安、教育部门双渠道进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后,工读学校则采取学生本人、学生家长和学生原先就读的学校三方自愿的招生方式。从立法的初衷看,这是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但因工读学校的“标签效应”太过显著,没有家长或孩子真正愿意去。专门学校就此萎缩,如今仍能招满生员的学校,很多都成为戒除网瘾的场所,已丧失法定的功能。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也没有借此得到矫治。
同时各地仍不乏有公安、教育行政部门强迫家长申请送孩子到工读学校的情况。而工读学校内开设的课程大多是矫正学生行为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学生的心理教育被忽视。更为糟糕的是,我见到一些专门学校像劳教所甚至监狱一样,不仅全军事化管理,还存在打骂学生,限制学生自由,甚至直接在学生寝室门口张贴“罪行卡”,用不同的颜色区别学生。甚至有的学生长达数月见不到自己的父母。这种与社会的隔绝会带来“交叉感染”,不良行为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与教育矫治的初衷背道而驰。
像大连杀人案的凶手更是这种“养猪困局”的体现,他的情况比工读学校中的学生严重,却没有合适的接受矫治的场所,我国亟待在“一放了之”和“一罚了之”之间建立中间性的“保护处分措施”体系。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社会建设委员会牵头,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目前修改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中。针对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学界有哪些建议?
姚建龙:类似大连杀人案的极端事件每隔几年就会被热炒一次,比如2008年时一个13岁少年强奸了一名女孩,因为没到刑事责任年龄,警察把他放了,放出来之后,他来到女孩家,当着女孩的面把女孩的妈妈杀了。又比如2015年湖南邵东的杀师案,三名中小学生抢劫小学宿舍楼,持木棒殴打女教师,并用布条堵嘴致其死亡,其中两个孩子是留守儿童。这些事件的屡屡出现,是这次修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实际上,司法系统处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重刑的比例并不多。比如2004至2009年间,未成年人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例为10.15%,到2014年这一比例仅为7.31%。约93%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如果有完善的保护处分措施“以教代刑”,大部分触犯《刑法》的涉罪未成年人其实并不需要判处刑罚。而像大连杀人案的凶手难以处理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罪错分级的保护处分措施加以覆盖。
保护处分措施的理念是“提前干预,以教代刑”。在我提供给全国人大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专家建议稿中,我建议将罪错行为分成四级:第一级是具有自害性质的不良行为;第二级是严重不良行为,我主张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第三级是触法行为,也就是因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第四级是犯罪行为,也就是符合《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
针对这四类行为,我在建议稿中建议,将现行治安处罚、专门教育、收容教养、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整合、改造,成为包括教育处分、观护处分、禁闭处分、教养处分在内的系统性的保护处分措施体系。对不良行为主要依靠监护人、学校和社区处理,尽可能避免动用国家强制性干预措施。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触法少年,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判决适用教育处分、观护处分、禁闭处分措施。对于严重触犯刑法的触法少年虽然不能适用刑罚,但可以适用教养处分措施,并且在高级专门学校执行,时间最长可以到该少年满20周岁为止。
面对触法行为的少年,可在放任和刑罚之间提供一个中间性措施,比如把罪错少年交付到一个公益机构、一个企业,或最好是一个志愿家庭,让他们帮助少年脱离原来的环境,强化对少年的监护、管理和教育。而如果罪错少年的状况还得不到改善,再将他送入少年院专门管理,比如将专门学校分级,招收不同罪错程度的学生。但这个少年院要谨慎地限制人身自由,更多扮演家庭式环境中的教育角色。
我注意到,正在征求意见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存在一大硬伤,那就是罪错行为分级中少了“触法行为”这个社会最为关切的一级,并且简单、直接删除了收容教养措施,更没有设计系统性的保护处分措施体系。这意味着,因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触法少年,仍然会面临“一放了之”的境况,或者面临修订刑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一罚了之”的危险。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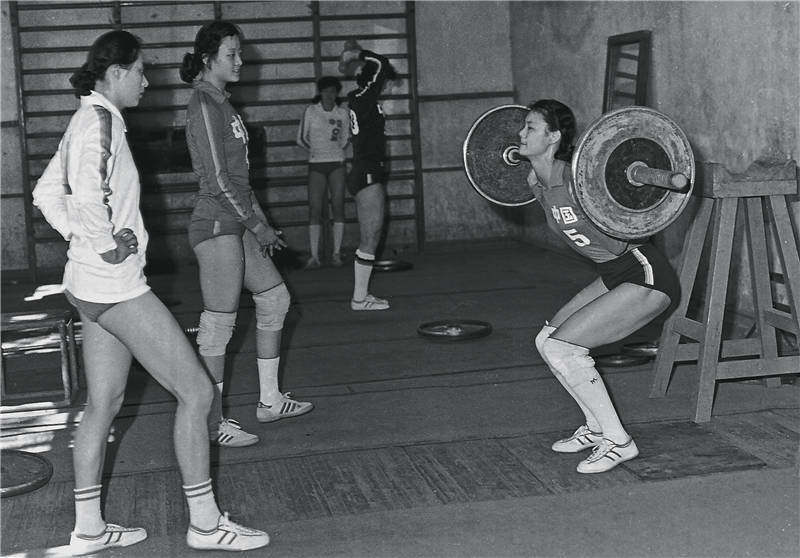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