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原来(写小说)是看实体之外留出多少空白,这次则是看空白之外留出多少实体。这些对他而言是全新的写作体验。
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A,而是B;也不是B,而是C。”刘氏句式,在本篇采访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2017年11月1日,刘震云最新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问世。与书名“吃瓜时代”相应和,出版方长江文艺当日把发布会放在了北京大兴御瓜园。宾主相逢人人发了一牙瓜,吃完瓜抹抹嘴,刘震云走上台来向众人躬了一躬,“西瓜是唐朝时从埃及传入中国的,但唐朝之前人们就吃瓜,这是肯定的。大家可能吃的是黄瓜、香瓜,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吃着瓜,围观、看热闹的心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吃瓜群众的语言便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就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问世前几个月,中国教育部曾召开发布会,介绍2016年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状况。会上“吃瓜群众”与“两学一做、冻产、表情包、洪荒之力”等名词一道当选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这多少可以视作主流社会对近些年热络于网络之上“吃瓜群众”看客心态的某种认可。
2012年推出《我不是潘金莲》,去年出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自言自个儿是写完了“告状妇女”,讲“吃瓜群众”。而两者间隔五年之久,却创下新世纪以来刘震云作品出版时序间隔之最——上世纪90年代,他曾花了八年时间创作长篇《故乡面和花朵》,是以当人打趣他这次是不是让读者等得太久了时,他把两手一抄正色道,“五年?这是我创作的正常周期。”
五年间文学作品付之阙如,可公众人物刘震云并没有淡出大家的视野。特别在前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且前后脚上映,风光势头可谓一时无两,2016年更在坊间被称为“刘震云年”。《南方周末》前记者张英,八年前一篇文章开头就写过刘震云的苦恼:先前采访他的都是读书版的文化记者,如今采访他的都是跑影视的娱乐记者,“他们甚至不看我的小说,或者把电影当成了我的小说。”
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例,2009年首印20万册,近十年来逐步加印,现在总印数已达230万册;五年前《我不是潘金莲》首印40万册,而今就达到了210万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首印是90万册,乍一听来好像不得了了,可我们一点都不担心。这其中固然有影视助推的因素,更关键的是刘老师的书不仅畅销,更长销。”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文学主编安波舜告诉笔者。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写了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
与作家的云淡风轻相比,评论界显然没那么淡定。“最大的感触是猛。”一篇在朋友圈广为传颂的书评如此写到。
“戏剧在舞台上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已经搬入了生活中。有这么多吃瓜群众存在,证明生活中的大戏接连不断。身陷其中的人可能痛不欲生。但吃瓜群众和这些人心态正相反,起高楼宴宾客的时候群众是厌烦的,楼塌了的时候吃瓜群众则乐不可支。”刘震云说。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写了四个人物,然而刘震云却说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吃瓜群众在小说中并没有出场,然而比吃瓜群众更重要的是,读者朋友是这本书的主角。这个戏这么好看,其实不是戏好看,而是这部戏背后的道理,道理和道理间的联系特别幽默且荒诞。”谈到读者反馈,刘震云说采访他的记者都已经读过这本书,“他们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就参与到这本书里来,把人物关系间的空白以及人物关系背后的联系,他们能说出自己的一番见解。”
让读者参与进文本的二次创作并不新鲜,然而一边厢看书中的人物“宴宾客又楼塌了”,一边厢看新闻某某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成为“2018新年首虎”,则是一番况味迥异的阅读体验。然而,同现实黏连太近,是否会减损文本自身的文学性?可能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要直面的一个问题。
“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过‘新新闻小说’的潮流。代表人物就是卡波特和梅勒,他们把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一个案件搬进小说,叙述与阐释的角度同大众视角并不相同,而是靠作家的敏锐逐步逼近涉事者的灵魂,从而折射出一个社会的荒诞。”安波舜说,当年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便是由他译介进国内出版。“结构上或许类似,但刘老师小说的笔法又是非常中国化的,你能读出其间“拍案惊奇”、《醒世恒言》的意味。”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不是官场小说,也不是反腐小说,而是探索这些官员的(李安邦、杨开拓)初心与他们后来‘不信马列,信鬼神’转折的一刹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之于农村妇女牛小丽以及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的命运,则关注到中国人普遍的一个劣根性。那就是当他们离开了熟人社会,离开了自己的村庄、工厂、机关、城市,置身于另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往往就可以‘出点格’,‘越越轨’。可能就是随地吐了口痰,也可能如牛小丽般出卖肉体或是如马忠诚般进了一次洗脚屋。而当他们回到自己的熟人社会则依旧该干嘛干嘛,本来是良家妇女,回来还是良家妇女。”安波舜说。
“荒诞肯定产生于现实。我的作品并不幽默,我这个人也特别不幽默,我书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特别质朴,我反感俏皮话,也反感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
在新书发布会现场刘震云说,他自言自己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197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刘震云在校刊《未名湖》上发表了个人处女作《瓜地一夜》,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在文学世界同“吃瓜”有所瓜葛。当时年轻美丽的学姐查建英是杂志主编,两人约定了在刘震云宿舍聊一聊稿子。刘震云特地备了茶包招待,查建英对3000字的小说前后提出了18条修改意见,刘震云当即满口答应。在接下来半个月里,刘震云反复回味了和查建英喝茶聊天的场景,然后把一字未改的原稿交了上去。小说发表后,刘震云问查建英文章修改得怎么样,查建英答:“修改得特别好!”
对话刘震云
距2012年推出《我不是潘金莲》,悠悠五年之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面世,是不是让读者们等得太久了?
刘震云:五年就我的创作来说,是正常的一个周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比写得快更重要的是要写得好。写得好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下一部要跟上一部不一样,这是进步的一个基本标准。不一样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跟别人不一样,一个是跟自己原来的作品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相对容易,跟自己(过往)不一样相对困难,因为写作跟干任何事一样有一个惯性,这个又跟开饭馆不一样,不管是宫保鸡丁还是锅塌豆腐,客人如果觉得菜的味道跟原来不一样了,以后也许就不来了。但创作就不一样,一部作品的人物、结构、语言的流动、味道、水准如果跟上一部一样就不是进步。
吃瓜群众是2016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是近年来的网络热词。它观照到了一个个具体的网络事件,我很想知道是不是这些事情触动了你的创作欲望?
刘震云:我动笔写一部小说从来不是因为一个事件触动了我,人们经常会问我从哪件事儿上触发了写作灵感?我的写作习惯是首先从故事的结构出发,起码应该有几件事、几十件事甚至是上百件事上千件事,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关系。当然,故事的结构关系对于写长篇小说来讲也不是特别重要,第三个层面,更重要的就是人物结构,就是一个小说里边到底都有谁。《一句顶一万句》有一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之间的结构关系是什么,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亲属关系,或者是工作关系,或者是生活中的联系,但是比人物结构更重要的是第四个层面,就是故事结构和人物关系背后的逻辑链条。这种逻辑关系代表一种人物关系的演变,固定的人物关系对于小说是没有用的,人物关系是在不断地往前演变的,能推动人物结构和故事结构的发展,这背后就是逻辑关系。对比这个逻辑关系,第六个层面有时候会涉及这背后的认识和思想,这对于小说来说太重要了,它涉及小说的思想内涵了。思想内涵必须演变成人物关系和故事结构,接着再打到情节和细节和语言上去,包括语言的风格和味道上去,如此形成一个深入和浅出的过程。文学确实不是哲学,但是哲学对文学又非常的重要,这之间的演变对于作者是非常重要的。我深知长篇小说的道理,所以我不会说在生活中有一件事儿触动了我,就要去张罗一个长篇小说,这不现实。
在阅读《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时,最大的一个感受是里面很多故事似曾相识,这个“相识”不完全是过去式,可能就在我们阅读的时候,又有一个类似的网络事件发生了。类似这样的阅读感受,你怎么看?
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会有一些巧合,有一些是我们在生活中能够遇到的特别有意思的事件,这个事件具体是那件事儿不重要,事件里面含的那个荒诞和幽默的成分特别重要,比如像《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里面一个桥塌了,官员过去的时候确实是吓傻了,人傻了的话一般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吓哭了,哭的极致却是笑了,当然这不是快乐的笑,是一种傻笑,但因为现在的手机太多了,这个瞬间被定格了以后,一个标题就会把它的意义转变,这个傻笑就变成了微笑,就出现了“微笑哥”。马忠诚在洗脚屋一节,这个洗脚屋跟当地联防大队是勾着的,这些细节都很有意思,我也注意到了,但是我把这些用到作品中并不是我要从这几件事本身出发,这是调查记者该干的事儿,而我是个小说家。小说家如果这样写小说,第一写出来它不成立,第二就是会带来很多的诟病,因为它确实构不成文学作品。
作为一个作家,你会关注到评论界以及媒体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吗?我这有个最新消息,“吃瓜”刚刚被《亚洲周刊》评为2017十大小说。
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出版之后,无论纸媒还是互联网上的媒体,评价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基本上说不好的很少,众口一词都说写得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不是从细节出发,不是从一件事儿出发,还是考虑了小说根本的东西。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一个作者写作的心态,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作家,在写一部作品的时候我总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初学者,对新的作品只有去咂摸出除了小说本身内容的滋味和写小说时候的新的心得和体会,滋味和味道,这就是一个重新开始。以前我写小说的话,人物关系是比较紧密的,不管是《一句顶一万句》还是《我不是潘金莲》,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我特别想写的是这几个人根本就不认识,八竿子打不着人背后的逻辑关系是空白的。过去是写实的东西看留了多少空白,现在写空白再看留了多少实的东西。这对我写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原来是实体留出多少空白,现在是空白留出多少实体。这些对我是全新的,创作全新的东西对一个作者而言,吸引力肯定是非常大的。
从《手机》到《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其实你早先就注意到了技术或者说科技对人的异化与改变,从当初的“手机就是手雷”到现在“由驴尾巴牵出棒槌,由假的牵出真的,由芝麻牵出西瓜”的吃瓜时代,你觉得社情民意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刘震云:读者对一个作者的要求当然是希望你写了那个能不能再接着写写这个,比如说写了《一句顶一万句》能不能再写一个《一万句顶一句》,写了《我不是潘金莲》能不能再接着写一个《我不是武大郎》,这样的写作当然也是成立的,问题是这样的写作,你真正开始写的时候一个是觉得没劲,还有就是无趣,那就是纯粹为了写东西而写东西,如果要是纯粹为了写东西而写东西我就不干这一行了,因为写作的根本的要求就是跟饭馆儿的做法不一样。我确实有两个想法,这两个想法我一直没有落实,没落实的原因是我还拿不出全新的东西来,比如当时写《一地鸡毛》的时候,有人说下一部最好写一个《一地鸭毛》,再来一个《一地鹅毛》变成“三毛系列”,这样写没什么不可以,但是这确实不叫写作,但是我确实是想再写一个长篇叫《鸡毛飞过三十年》,这一定特别值得写,我一定要写出来,原来的小林变成了老林,因为小林在写作的过程中跟我处过很长的时间,小林这三十年怎么样,他的老婆怎么样,女儿怎么样,他办公室的老张、老乔这些人怎么样了——因为都是过去的老朋友,我特别想知道。我只是知道这些人现在是什么样子,但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全新的人物结构,包括背后的思想逻辑,这是我迟迟没有动笔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这个东西不可以写。《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跟《手机》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最重要的还是小说的结构,《手机》是实体留出来的空白,《吃瓜时代》是空白留出来的实体,《手机》最想说的一个逻辑是谁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我们过去总是讲社会的改革、政治的改革都会带来社会的进步,这些年给我们的启示是恰恰不是这些,因为那些东西会回头,因为这个社会,包括政治和生活,换了不同的人可能突然就返潮了,但是科技是不断地往前走的,科技确实能够给人带来新的生活形态和新的生活方式。我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手机和互联网、微信微博朋友圈,过去山沟里发生的一件事儿只有山沟里知道,现在有了手机马上全天下就知道了。如果不是有手机,这个杨开拓在大桥上笑了一下,这个瞬间就过去了,但是手机把它变成了微笑,互联网微信和微博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过去是让你知道什么你才能知道什么,现在是所有人的话都可以让大家知道,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自媒体的力量,自媒体的力量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民主,每个人都可以说话。
作为一个人文作家,你怎么看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者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刘震云:科技是拯救,也是改变,一部作品出版之后会有对这个作品的很多的留言,这个留言有时候就是一个人个体说出来的,这不就是民主吗?我庆幸也特别感动的是我的作品出来之后发现大家都是善意的,这种善意就更加深了我写作的动力。我看到有一个人说,有两个人出了作品的时候说好话的人多一些,一个是我一个是李安,我觉得这是一种善意和表扬,更重要的对作者是一种鞭策,证明这个作品在写之前确实有过全新的思考,下一个作品就更要有全新的思考。科技改变人的生活是《手机》所反映的最主要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推翻了前人的认识。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尼采、维特根斯坦、康有为、梁启超、鲁迅,他们觉得改造国民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的改革以希图推动人类历史进步,但是最后你会发现都不是,就是互联网和手机的出现,这是很重要的,就像《一地鸡毛》一样,和我现在写《鸡毛飞过三十年》又不一样,《手机》是我零二年写的,这十五年互联网的变化也非常大,过去手机就是收短信发短信,现在的手机是收发微信,微信最厉害的地方是可以形成朋友圈,朋友圈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了不得,民主的实现就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每个人都可以发言,朋友圈的前进是说,我们几个的发言别人听不到,而且一个人可能有十几个朋友圈,而且朋友圈的叠加和化学反应是非常神奇的。我们经常会说到“低头族”的观点,我觉得如果大家这么爱看的话就说明手机里的内容是非常有意思的,朋友圈是非常有意思的。虽然朋友圈中说的这些事儿未必真实,但是语言的习惯和关注的事儿的方向确实跟新闻联播是非常不一样的。
从牛小丽到马忠诚,这些不相关联的人物身上其实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为了一句话非要刨根问底,这一点和前作李雪莲的性格悲剧也非常相似。我很想知道,你如此刻画人物,是小说情节推进的需要,还是就源于你个人的一个“情结?
刘震云:对一句话特别较真儿,来源于我对人物的认识,这个东西推动不了故事的情节,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其实这样的人物是我非常敬佩的,比如说李雪莲,她的身份不是默克尔,也不是希拉里,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但是她能够为了一句话对全世界宣战,能够为了这句话宣战20年,这时候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民族英雄,民族英雄不应该只是像董存瑞、邱少云这样的人,还有好多特别普通的人,甚至他们的韧性有时候甚至要比做一时的英雄更需要坚定的信念。
现实中你是否就是一个会为一句话较真的人呢?
刘震云:我肯定是一个这样的人。
很多读者看完小说会为牛小丽的结局鸣不平,可以说继李雪莲之后你又创造了一个人们心疼的女性。
刘震云:有时候读作品是一种心情,但是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个结构。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说看到牛小丽最后的结局都于心不忍的,但作者就是要从更宏观的层面,从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考虑。牛小丽的结局在生活中也是存在的,就像是蘸饺子的那种醋,这个结局也是一个醋,现实中也有“赵红霞事件”,大家在生活中也都于心忍了,吃瓜群众甚至都在把她当一个笑话儿在说。还有很多读者说,我把李安邦老婆的结局写得好惨,我觉得这个“好惨”可能会是一种生活评价,可能会是一种道德评价。但如果你翻一翻过去的历史,比方说当一个王朝被推翻的时候,这些皇亲国戚都怎么样了?一个是与披甲人为奴,另外一个就是满门抄斩。从历史上看这些都太正常了,我写的是现在的故事,可是着眼点可能是在历史上扎着。这样来看我觉得像李安邦的老婆的这种结局也很正常,远的不说,从“文革”到现在,凡是一个官员倒台的时候,他的家属都在干什么?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很多读者在《吃瓜》中读出一种悲悯,特别是你除了写一个小老百姓,更写了三个各自有着不同污点的官员,但似乎你都保持着一种悲悯的态度。
刘震云:我看到“吃瓜时代”的很多的读者的留言,说我作品里的贪官和新闻里的贪官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书里的这个贪官确实是有血有肉,他一步步地走到贪官的路上有时候是客观的各种因素的促成,有时候是他主观的因素,这个跟新闻里的贪官有很大不同,作品里的贪官是一个人物。曾经给我的一个颁奖词我觉得是挺对的,就是“老辣之笔,慈悲之心”,“慈悲之心”并不是说要同情谁或者怜悯谁,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世界确实是多面的,一个人也是、一件事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我的作品里的人物肯定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有趣不止是生活中的趣味,而是性格的不同侧面,组成的这种相互映照出的特别微妙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比如像“吃瓜时代”里的这个贪官,是特别有意思的人,如果不是贪官的话在生活中一定是一个特别有见识的朋友。李安邦特别爱到江边的小饭馆吃饭。凌晨两点到,小饭馆老娘说:您又来啦,当个省长也不容易。他说:我不容易就一天,你这天天都开到这么晚。吃饭的人见他说:省长来体察民情啦。他说:我就是来吃个饭,你们还联系到工作上去了,还是你们觉悟高。老板娘说:听说这个小饭馆要拆了,他知道城建部门确实有一个规划,要在江边搞一搞,亮过美国曼哈顿。他说:没事,拆了我再给你找一个地方,比这里还好。老板娘说:这下我能睡踏实了。他说:我这可不是为了你,你这饭馆没了我去哪儿吃饭呢。这样的情节很真实,也特别有意思。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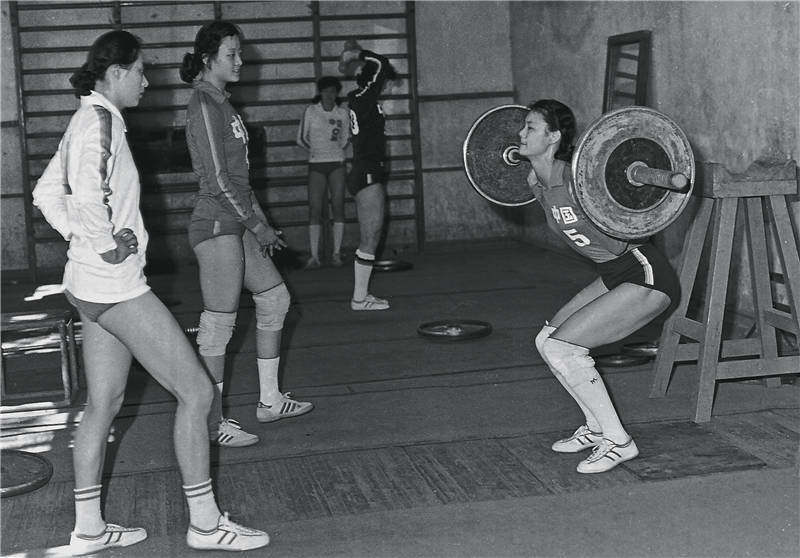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