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初的一个晚上,和几个朋友在蓬蒿剧场看了一出话剧《审判寄生虫》。话剧改编自俄语诗人布罗茨基在1964年被苏联当局以“寄生虫”名义加以审判的一段史实。当时的布罗茨基只有22岁,写作并翻译了少量诗歌,然而这场卡夫卡式的审判,却让他在全世界声名大噪。声援来自对集权体制的共同恶感,起初是阿赫马托娃及彼得堡诗人圈里的朋友,随着记者维格多罗娃将受审实录流传到境外,BBC很快播放了据此改编的广播剧,布罗茨基的事迹开始广为人知。
两个小时的话剧,虽以审判为主要线索,穿插其间的诗句、独白,却将时空推向布罗茨基一生中所有的重要节点。对像我一样起初并不够了解这位诗人的人来说,话剧简直是一堂信息量密集的文学课。然而,交叉路径的汇合处是反抗,是桀骜的青年诗人面对庭审时的那份不羁还有无奈。不妨看看下面这段记录:
法官:您的职业是什么?
布罗茨基:诗人。诗歌译者。
法官: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是谁把您列入诗人行列的?
布罗茨基:没有人。(并非挑衅地)那么是谁把我列为人类的呢?
法官:那您学过这个吗?
布罗茨基:什么?
法官:学过怎样成为诗人吗?您没有上过大学,那里培养……那里教出……
布罗茨基:我不认为诗人是教育出来的。
我们或许该庆幸解冻之初的苏联还留下了这样一份诗歌档案,供我们辨认一位诗人的成长线索。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段布罗茨基的独白:“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即是说,某种难以虚假、伪装、模仿的东西;某种甚至连老练的江湖骗子也会不高兴看到的东西。换句话说,即是某种像你自己的皮肤般不能分享的东西:甚至不能被少数人分享。”

不论如何,诗人因为缺乏稳定的工作,被认为是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最终被判决劳教5年,虽然在各方努力下,他最终在流放地,一个叫诺连斯卡亚村的集体农庄里待了18个月。在传记作者谢洛夫笔下,那是布罗茨基沉潜于诗学的一段时光,布罗茨基本人在一次谈话的回忆也颇有意味:“我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之一。没有比它更糟的时候,但比它更好的时期似乎也没有。”
尽管如此,布罗茨基后来很少回忆这段经历,部分原因在于,他与波兰诗人米沃什一样,拒绝将自己放在受害人的位置上,做廉价的哀悼;部分原因也在于,他有意疏离于这段经验,因为一些不公正的言论指出,布罗茨基的世界声望并非来自他的诗作,而是来自他的受审。
当然,布罗茨基本人肯定不屑如此作想。关键词在于疏离,在于他早在幼年便养成的人生态度,后来不过是越走越远罢了。我有时想,抛开布罗茨基的那些诗篇,他的那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哲学识见无疑走得更远。在为诗一辩的伟大传统中,布罗茨基的声音震耳发聩:诗歌,在难言的激情中发明与延续语言,美学先于伦理,而“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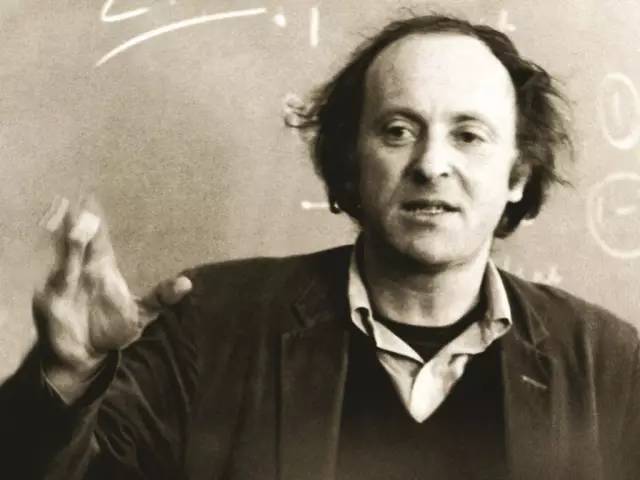
美学经验首先来源于对现实与存在的疏离。在那篇自传体散文《小于一》中,布罗茨基记录了少年时代的思想碎片:“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想到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
布罗茨基尝试疏离的第一步是,主动忽略掉课堂内外无处不在的领袖画像:有金黄色鬃发像天使一样的婴孩列宁;秃头、紧张的二三十岁的列宁,以及一些变体,带着工作帽的,别着康乃馨的,穿着马甲的列宁;后来是斯大林,活着的尚且没有得到历史赞助的斯大林。布罗茨基坦言自己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以至于他将任何表示重复的东西,便视为一种必须铲除的损害。“只要是大量的,我便立即把它视为宣传。”而“基于某种理由,过去不像未来那样辐射如此巨大的单调。未来因为其大量,所以是宣传。杂草亦然。”
这当然是美学的态度,也是诗歌的态度,却向我们透露出某种自由的奥秘,发现(对所有表达未表达出的诗歌尤为重要)的眼光需要对现实的某种陌生化,面对大量重复的沉闷,人们需要疏离,需要转身,换言之,需要重新发明现实。

或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能理解监狱中困守二十年的安迪,终生将自己囚禁于海上的钢琴师,又或者,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小镇的康德。然而,这并非无所作为,并非一种自欺欺人的生活艺术化。布罗茨基的态度理性而进取,虽然美学经验永远摆在第一位。在1984年威廉斯学院的毕业典礼致辞上,布罗茨基以亲身经历,提供了一种身处极端环境中对抗恶行的作为——面对监狱看守无礼的规则,劈光放风场里的所有木材,否则没饭吃。一名二十四岁的囚犯连续砍了12小时木材,让看守最终变得迷惑而恐惧——“可以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它表明,通过你大幅度的顺从来压垮恶的要求,可使恶变得荒唐,使伤害失去价值。”
阅读本身也是训练疏离艺术的重要途径,它让一个人保有一张表情独特的面庞。更重要的是,对文学的阅读,本身就是对恶的抑制。在那篇著名的诺贝尔授奖词中,布罗茨基说道:“我只想说——不是凭经验,唉,只是从理论上讲——我认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就更难为着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我谈的正是对狄更斯、司汤达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巴尔扎克、麦尔维尔等等的阅读,也就是说是谈对文学的阅读,而不是谈识字,不是谈教育。识字的人也好,受过教育的人也好,完全可能一边宣读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论文,一边杀害自己的同类,甚至还能因此体验到一种信仰的喜悦。……”

写作当然也是。只是,正如布罗茨基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每样事物都有其局限,包括忧伤”,仅仅累积没有把握的写作,面临的局限更多。平庸与伟大,拘谨与自由之间的分野,似乎就在布罗茨基1965年6月13日写给诗人雅科夫·戈尔丁的那封信中:
“看待自己的时候不要去与其他人作比较,而要天马行空。要天马行空,让自己为所欲为。如果你愤怒了,那么就别掩饰这一点,让它粗鲁下去好了;如果你开心,同样不要掩饰,就让这开心老套好了。要记住,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不是任何人的生活,即便是最崇高的规则,也不是为你而立的法律,这并非你的规则。它们至多不过像是你的规则。要独立。独立性,这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是一种最好的素质。就算这一点会把你引向失败,这也将仅仅是你的失败。你自己去与自己算账;否则的话,你就不得不去与鬼才知道的什么人算账。”
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1980年5月24日,在生日那天,布罗茨基以一首诗回顾了自己40岁的生活——
“由于缺乏野兽,我闯入铁笼里充数,
把刑期和番号刻在铺位和椽木上,
生活在海边,在绿洲中玩纸牌,
跟那些魔鬼才知道是谁的人一起吃块菌。
从冰川的高处我观看半个世界,尘世的
宽度。两次溺水,三次让利刀刮我的本性。
放弃生我养我的国家。
那些忘记我的人足以建成一个城市。
我曾在骑马的匈奴人叫嚷的干草原上跋涉,
去哪里都穿着现在又流行起来的衣服,
种植黑麦,给猪栏和马厩顶涂焦油,
除了干水什么没喝过。
我让狱卒的第三只眼探入我潮湿又难闻的
梦中。猛嚼流亡的面包:它走味又多瘤。
使我的肺充满除了嗥叫以外的声音;
调校至低语。现在我四十岁。
关于生活我该说些什么?它漫长又憎恶透明。
破碎的鸡蛋使我悲伤;然而蛋卷又使我作呕。
但是除非我的喉咙塞满棕色黏土,
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黄灿然 译)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