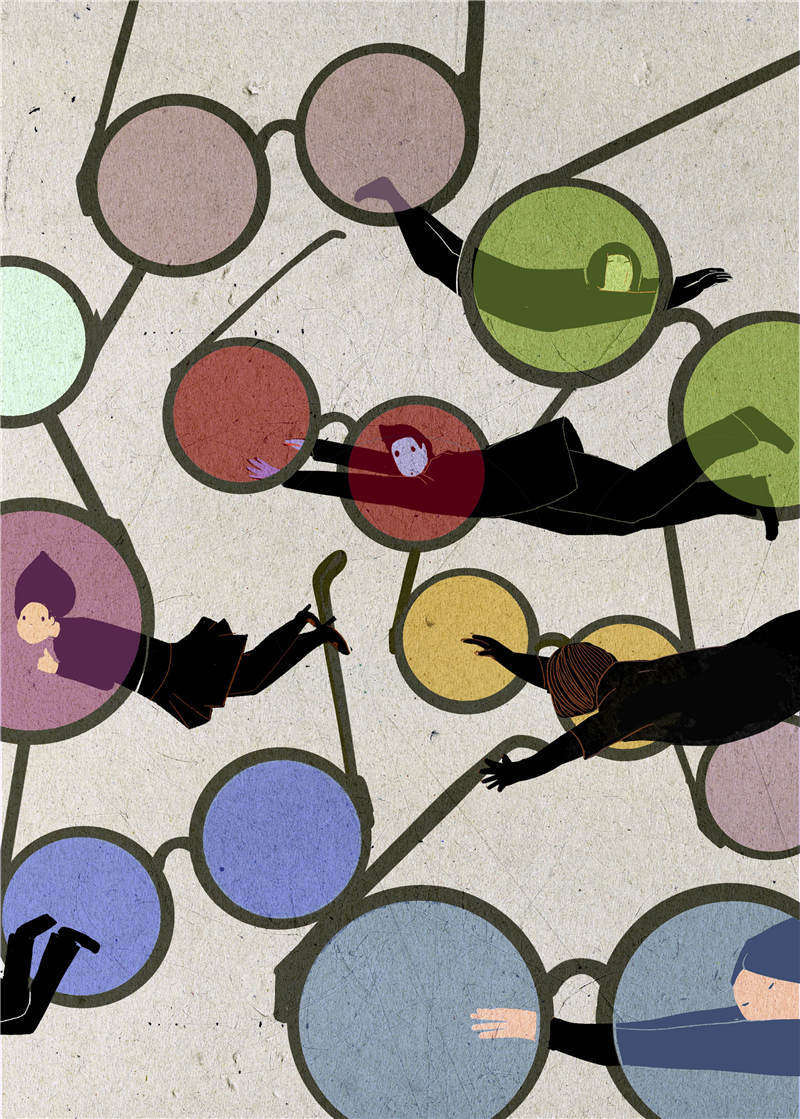
(插图 范薇)
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这样的:一个父亲和儿子出了车祸。父亲当场死亡,男孩重伤并被送往医院。在医院里,主刀医生看了一眼男孩说:“我没法给这个孩子做手术。他是我儿子。”
请问,既然他的父亲已经死亡,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和我一样,想了很久没想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恭喜你,你是一位隐秘的性别歧见者。
因为正确答案是,这位医生是孩子的母亲。
至少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颇为醍醐灌顶的时刻,就好像你突然触摸到生命潜流中的某处陷阱,或者感受到一阵沉钝的刺痛感——关于性别的偏见如此深刻地内化到我们的日常思维之中,仿佛一根刺,直到此刻才传递出痛感。
和所有脊椎动物一样,人类双眼的视网膜上有一个盲点,这个区域叫作scotoma(希腊语的原意是“黑暗”),意思是没有对光敏感的细胞,因此虽然光照射在此处,却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被大脑的视觉区域所感知。
同样,心理学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发现了大量的认知偏见与盲点,其中最有趣的,是关于内隐性社会偏见的研究。这些关于种族、年龄、性别等特征的偏见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交往过程之中,往往是我们的大脑自动而隐蔽的计算,但却在情感与行为层面对个体和社会都产生重大而隐秘的影响。
一岁的婴儿已经能区分不同的种族,并且能将熟悉的面孔与愉悦的音乐联系起来。到了六岁,孩子对于自己的偏见很坦率,到了十岁,他们开始戴上社交面具,开始隐藏一些自动化的感受。到了成年,大部分人都会发誓自己没有偏见,直到某些特殊的场合,比如听到刚才那个脑筋急转弯。
什么是偏见?偏见是如何形成的?它与社会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到底是偏见塑造了文化,还是文化塑造了偏见?如果说偏见是一颗种子,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那么在什么样的土壤里,它会生根发芽?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控制它?网络时代又为我们的偏见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是我们这一组封面故事希望解答的问题。
认知:我们vs他们
在《社会性动物》中,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提出,偏见有三个层次:认知的,情感的,行为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对同性恋有偏见时,我们的意思是,他(她)对他们有先入为主的看法,对他们有负面的情感,并且倾向于带着成见或敌意来对待他们。”
在认知的层面上,偏见是你对世界的看法,对他人的看法,这些看法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但总体上是一种先入为主,或者以偏概全。
在情感的层面上,偏见会激发喜欢/讨厌、爱/恨、恶心/嫉妒等复杂的情感,这些情感又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和行为。
在行为的层面上,偏见往往会导致歧视,甚至污名化。在现代社会,大多数形式明确的歧视都是非法的,但偏见仍然可以以微妙但重要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美国,最严重的可能是种族歧视,而在中国则是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导致的歧视,比如农民工曾经被称作“盲流”,这就是歧视性的称谓,是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导致的。性别歧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类别,我的采访对象之一、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严飞说,他对于中国当下电视剧中的一种剧情套路深为不解:为什么现代女性必须经历“斗小三”的磨练之后才能成长为独立女性?
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观察到,二元对立(男/女、善/恶、热/冷、保守/自由、人/动物、身体/灵魂、自然/人工培育等)是人类最简单也是最普遍的应对自然界复杂性的方式。
这种分类倾向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生活。我们/他们就是最基本的分类——我们是中国人,他们是外国人。我们是城里人,他们是乡下人。我们是中产阶级,他们是穷人。我们是女人,他们是男人。我们是好学生,他们是坏学生。我们是基督徒,他们是异教徒……

美国生物学家罗伯特 · 萨珀尔斯基
在《行为》一书中,美国生物学家罗伯特·萨珀尔斯基提到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情:在《人猿星球》的拍摄现场,扮演黑猩猩的群众演员与扮演大猩猩的群众演员在吃午饭时居然很自然地分成两桌。于是,他引用了一句笑话:“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把人分成两种,另一种则是不这样分的人。”
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分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捷径。或者,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的说法,这种分类依据的是“最少努力原则”(least effort principle)。
对我们的祖先而言,在一个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求生存,把陌生人当作潜在的攻击者,而不是善意的朋友来对待,显然有更好的生存几率。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对小型社会的生活方式充满了浪漫的幻想,认为他们在道德的许多方面上都要远远优于当代社会之人。但她在谈到他们对陌生人的态度时,立场就不那么坚定了:“大多数原始部落成员都觉得,如果他们在丛林中偶然遇到来自敌对部落的‘亚人类’,那么最恰当的做法就是把他乱棍打死。”即使人类文明进化到今天的地步,我们在遇到陌生人时的第一反应仍然不是仁慈友爱,而是恐惧、厌恶,甚至是仇恨。
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大脑在做出我们/他们的区分时,速度十分惊人。比如,以每秒20张的速度给你看一组照片,几乎是一闪而过,你的大脑也能立刻区分出我们/他们——如果照片里是“他们”,就会立刻触发杏仁核的反应,也就是负责恐惧、焦虑和攻击性的大脑区域。给你看一段有人被针扎手指的画面,你的大脑会产生“同构反射”(isomorphic reflex),此时大脑运动皮层对应手的位置会兴奋,进而你的手会握紧,好像感受到了对方的痛楚,除非这只手属于一个异族者。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
阿伦森说过,一旦我们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就会以标签化的方式来总结群体的本质——这就是“刻板印象”。
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术语的人,他描述了现实世界与我们脑中的“镜像”之间的区别。“刻板印象”就是让这些镜像支配我们的思维,产生期望,塑造我们构建的关于人们及其行为的叙述。
他曾经说过,我们绝大部分的偏见和成见,都是源于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先看到,然后定义。而是先定义,然后看到。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关于“我们”的刻板印象,总是自吹自擂式的——我们更正确,更聪明,更道德,更值得的;我们的食物更美味;我们的音乐更动人;我们的语言更有逻辑,或者更富有诗意……
关于“他们”的刻板印象,则常常是负面——他们危险、愚蠢、不可信赖,他们道德败坏,他们吃昆虫……
在“我们”内部,我们尊重个体的丰富性,关注他们的变化,但对于“他们”,我们很少考虑一个人作为个体的复杂性,而只是将其视为一个范畴,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他们只是他们的黑皮肤、性别、性取向……他们情感简单,对痛苦也不敏感。无论在古罗马、中世纪英格兰、古代中国,还是美国旧南方,精英阶层都理所当然地给奴隶们塑造了简单、幼稚、无法独立等刻板印象。
当“我们”犯错时,我们会更倾向于原谅,找各种借口为之开脱:一般来说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犯错一定是局势所迫。而当“他们”犯错时,我们相信这件事反映了他们的本质: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并将永远保持这样。
神经学关于催产素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种护短和排外的现象。我们一般对于催产素的认识是,催产素是关于信任,关于表达,关于亲社会性的激素。但很不幸的是,只是在那些被你界定为“我们”的人之间。当对方是那些被你界定为“他们”的人时,催产素反而会让你对他们表现出更多的恶意和恐惧,攻击性更强,而合作性更少。
荷兰有一项研究,实验者设置了典型的“电车难题”——假设你看到一辆刹车坏了的有轨电车,即将撞上前方轨道上的五个人,而旁边的备用轨道上只有一个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五个人会被撞死。你手边有一个按钮,按下按钮,车会驶入备用轨道,只撞死一个人。你是否应该牺牲这一个人的生命而拯救另外五个人?
一般来说,人们都愿意以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拯救五个人的生命。但如果你给备用轨道上的那个可怜人取个名字,再给实验对象注射催产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如果你给那个人取的名字是一个荷兰人的常见名字,比如德克或者彼得,实验对象就不大愿意牺牲他一个人来救另外五个人。但如果这个人的名字是荷兰人普遍有敌意的德国名字或者穆斯林名字,人们则很轻松就做出牺牲他的决定。
还有多项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种族同胞的面孔有更多含蓄隐晦的偏爱,对其他种族人痛苦的反应就更弱。也就是说,催产素事实上夸大了人们大脑里“我们vs他们”的分野。
情感:隐秘的直觉
阿伦森认为,一个有着深刻偏见的人对与他(她)所珍视的刻板印象不符的信息通常是免疫的。他引用法理学家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关于偏执狂的比喻,他们的思想就像眼睛的瞳孔:“你往它上面洒下的光越多,它就越收缩。”
为什么会这样?他认为,这与偏见的第二个成分——情感有关。
偏见虽然是一种认知捷径,但从根本上来说,情绪和直觉才是它的核心元素。正如奥尔波特所说:“尽管可能在智力上被击败,偏见在情感上依然存在。”
李普曼也提出过,刻板印象的表现形式从来不是中立的。“它不仅是用井井有条的方式替代现实的庞杂喧嚣的混乱状态。它不仅是一条捷径。它是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它是对我们自尊心的保护,是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我们自身的立场和我们自身的权利。因此,成见充满了被它们所吸纳的情感。它们是我们传统的堡垒,在这个堡垒的庇护下我们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坚持我们的立场。”
罗伯特·萨珀尔斯基则在他的书中提供了大量实验证据,显示我们对“他们”的认知看似理性,实际上却是被无意识操纵的。比如,让被试观看某个未知国家的幻灯片,如果在幻灯片切换间隙以极快的速度展示带有恐惧表情的照片,实验结束后被试会对这个国家有更多消极态度。坐在难闻的垃圾旁边,会导致人们对“他者”的争议性话题持更保守的态度(比如,异性恋对同性恋婚姻的态度)。刚从教堂走过的基督教徒会对非基督教徒的态度更加消极。在另一项研究中,在以白人为主的郊区火车站,请通勤者填写关于政治立场的调查问卷。研究者在半数火车站安排了一对墨西哥年轻人,穿着保守,在站台上低声交谈,并让他们连续这样出现了两周。两周后,他们发现,因为墨西哥年轻人的存在,被试更加支持削减墨西哥合法移民的法案,以及把英文设为官方语言的政策,而且更加反对非法移民的特赦政策(但等车人对亚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和中东人态度不变)。而女性在排卵期会对他者群体的男性持消极态度。
可见,我们对“他们”的本能观点和情绪反应,其实是被某些潜在的隐性力量所塑造的。无论偏见也好,看似理性的归因也好,不过是我们的认知和逻辑急于跟上情感的自我而编造出来的故事而已。这也算一种“确认偏误”:我们更擅长记住佐证而非反对自己观点的证据;验证时更倾向于支持,而非推翻我们的假设;以及更倾向于用怀疑的态度检验我们不喜欢的结果。

心理学家马扎林 · 巴纳吉
但是,心理学家马扎林·巴纳吉和安东尼·格林沃德编制的内隐关联测验(IAT),却似乎可以揭示我们那些隐秘的偏见。
它的操作程序如下:你坐在一个控制台上,看到一系列你必须尽快分类的面孔,比如说,出现黑人面孔按左键,出现白人面孔按右键。现在你必须对一系列积极或消极的单词做同样的事情:按左键表示积极的词(如胜利、快乐、诚实),按右键表示消极的词(如魔鬼、蛆、失败)。一旦你掌握了这些分类任务,面孔和单词就会结合起来。现在,当你看到一张黑人面孔或一个肯定的词时,你必须尽快按左键;当你看到一张白人面孔或一个否定的词时,你必须按右键。你会得到一组快速的组合:黑色+胜利,黑色+毒药,白色+和平,白色+仇恨,等等。随着时间的增加,配对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他们的研究一再发现,当白人的脸与正面的词配对,而黑人的脸与负面的词配对时,人们的反应会更快。这种速度差异据说是衡量他们对非洲裔美国人含蓄态度的一个指标,因为他们的潜意识很难将非洲裔美国人与积极的词汇联系起来。IAT的版本已经使用了许多目标群体,包括年轻人或老年人、男性或女性、亚洲裔或白人、残疾人或非残疾人、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肥胖者或消瘦者。
世界各地1500多万不同年龄和不同行业的人在网上、学校或在工作场所参加了测试,大多数人都认识到自己持有潜在的偏见。其中包括《纽约客》的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他是一个混血儿,同样震惊于他在内隐关联测验中的反应,“我生命中最爱的人(母亲)是黑人,我在这里接受了一项测试,坦率地说,我对黑人并不太残忍,你知道吗?”
我自己也尝试了一下。当我被要求在“男性”与“事业”、“女性”与“家庭”之间进行匹配时,任务完成起来非常顺畅,但是,在相反的联想任务——“男性”与“家庭”、“女性”与“事业”中,却变得寸步难行。
关于内隐关联测验的准确性,心理学界仍然有很多争议。但如阿伦森所说,“许多真诚地认为自己没有偏见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会带有偏见。当这些人与他们对之持有内隐负面情绪的人交往时,他们可能会感到不舒服,并且以微妙的方式表达这种不舒服,而这种方式是接受者能够感觉到但却无法清晰地加以辨别的”。
他认为,人们更容易暴露偏见的一个条件是精神疲劳,也就是当人们疲倦、喝醉、分心、害怕、愤怒或做任何消耗或分散他们认知资源的事情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借助他们的刻板印象。

他者的消失
但是,内隐关联测验给我们的另一个启发在于,这些刻板的、有失公允的“联想”到底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系统化地植入我们的日常思维和情感之中的?
很多心理学实验告诉我们,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制造恐惧/厌恶,制造“他们”,在“他们”与恐惧/厌恶之间建立关联,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偏见的种子之所以能生根、发芽,是否就在于我们允许自己对未知的恐惧,投射到对他人的看法之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觉得自己不仅是在战胜未知,也是在简化世界,创造一种可预测性。
40多年前,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亨利·泰弗尔设计过一个实验,根据对保罗·克利和康定斯基画作的偏好将实验对象分成两组,而且这种分组完全是无中生有。但实验显示,这样的分类之后,人们对自己的组员很友好,却对另一组的人相当苛刻。此后,为数众多的实验都向我们揭示,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文化身份的标记都能够让人产生对“他们”的敌意——甚至连随机分配的衬衫颜色都能做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这种对“他们”的敌意,似乎又与我们天性中高贵的另一面紧密结合,即大规模合作能力与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例如为自己所属的群体而战,甚至牺牲生命。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指出,对自己群体的爱与对异类的敌意很可能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了一种善良与暴力混杂的奇特局面——“就像一半是慈悲的特蕾莎修女,一半是战斗的兰博。”
是的,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是的,我们信任与我们相似的人。但这意味着我们必然要仇恨和鄙视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吗?
在《他者的消失》一书中,韩国哲学家韩炳哲哀叹,他者(der Andere)的时代已然逝去。那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地狱般的、痛苦的他者就此消失。如今,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同质化的扩散形成病理变化,对社会体造成侵害。使其害病的不是退隐和禁令,而是过度交际与过度消费,不是压迫和否定,而是迁就与赞同。
他说,同质化的恐怖(Terror des Gleichen)席卷当今社会各个生活领域。人们踏遍千山,却未总结任何经验。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人们渴望冒险、渴望兴奋,而在这冒险与兴奋之中,人们自己却一成不变。人们积累着朋友和粉丝(Follower),却连一个他者都未曾遭遇。社交媒体呈现的恰恰是最低级别的社交。
崔斯坦·哈里斯——硅谷著名的“叛徒”工程师曾说,目前互联网上出现的绝大部分问题都是源于技术的权力与人类心智的限制之间越来越大的不对称性。
在注意力经济的军备竞赛中,整个行业一心想要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用户注意力,让用户在自己的地盘上停留最多的时间。
什么样的内容能得到用户最多的参与度?
他的答案是“道德义愤”。Twitter上每一个与道德义愤有关的单词,都会极大增加转发率。YouTube高频关键词排行榜上排在最前面的,分别是“恨”“揭穿”“毁灭”“破坏”。
什么样的想法最容易传播?
他说,短平快的文字,而不是复杂、微妙的长文。140字主导着现代社会的议程讨论。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真正重要的话题是复杂的。而复杂的问题,从来就没有简单的答案,可以让所有人都同意你。人们无可避免会误解,或者为你的言论而憎恶你,进而演变成网络暴力。所以说,世界的两极化,是内置于互联网注意力经济的商业模式之中的。
为什么这个世界越来越疯狂?
“因为我们不断地被运送到网络上的疯狂之所,而不是可以冷静对话的公共空间。”
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严飞告诉我,中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当理性的声音渐渐消失,剩下的只有两极化充斥着情绪的噪声和偏见。他说,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社会学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叫“悬浮社会”。
什么是“悬浮社会”?
“就是没有根基,或者根基不牢,脆弱易碎,大家都处在一种非常焦躁的状态之下。整个社会像一辆高速运行的列车,就像重庆万州的那辆公交车,或者贵州的那辆公交车,我们不是司机,也不是抢方向盘的乘客,但我们无可避免都在同一辆高速运行的车上,稍有偏差就会出轨,就会掉下去。”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每个人都想短时间内成功,短时间内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短时间内在朋友圈里获得大量的点赞,与豪车合影,与名人合影,去网红地打卡,你的关注度迅速上升,上升之后整个人就会很‘飘’。”
“另外一种‘漂’,是在城市里打工的年轻人。他们每天996,上班很辛苦,回到家很疲惫,很焦虑,但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办法总结,也没有办法思考。第二天一早爬起来,从通州到国贸一个半小时,或者挤在地铁站里,被后面的人推着上地铁,然后开始新的一天,周而复始。”
所谓“零工经济”,今天做的不开心就换一家,不需要培训,对未来没有规划,也没有期待。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大家不愿意认真思考,信息获取的渠道非常短平快,躺在沙发上刷刷抖音、快手,看一些偏激的或者心灵鸡汤的公号文章,久而久之,认知上变得越来越懒惰,满足于被喂养的状态。
韩炳哲用“毫无节制的呆视”来形容这种社会感知模式——商家持续不断地为消费者提供完全符合他们欣赏品位的、讨他们喜欢的电影和连续剧。消费者被饲以看似花样翻新实则完全相同的东西。同质化的扩散不是癌症性质的,而是昏睡性质的。它并未遭遇免疫系统的抵抗。人们就这样呆视着,直至失去意识。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