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需要哲学吗?
“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八九岁时,维特根斯坦开始产生这样的困惑。后来的他意识到,这或许是他人生中第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面对这个无解的问题,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认真思考起来,尽管得不出任何答案。
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修斯(Gareth B. Matthews)写过这样一个小故事:6岁的蒂姆(Tim)问爸爸:“怎样才能确定这一切不是一场梦呢?”爸爸惊叹地意识到,儿子提出了一个最古老的哲学难题,这个难题足以让罗素、笛卡尔等一众哲学大家头疼。在经过一番对谈后,小蒂姆给出一个推断:“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那我们是不可能对一场梦做出提问的。”——作为这场谈话的暂时性收场。
当维特根斯坦产生对撒谎的思考时,他还是一个孩子,没有真正走进哲学领域;当蒂姆提出有关梦的问题时,如果父亲不是一个对发问很敏感的哲学家,也很难意识到6岁的儿子提出的是一个哲学问题。事实上,这两个场景都已经进入了“儿童哲学”的范畴。
类似的场景每天都会发生在不同孩子身上。一个4岁的孩子平均每小时会问20到30个问题,上学之后这个数据就会急剧下降。孩子需要哲学吗?这并不构成一个问题,无论是否需要,在孩子每天提出的无数问题中,总有几个问题可以成为严肃哲学领域中的真问题;当孩子提出问题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思考下去时,他就已经进入了哲学境地。
从中文译名上来说,“儿童哲学”究竟是给儿童的哲学、研究儿童的哲学,还是用哲学的方式进行儿童教育,抑或是还有其他的理解?这个概念显得很模糊。
儿童哲学发展至今,不过50多年的时间。那位意识到儿子蒂姆发出哲学提问的马修斯,被看作西方儿童哲学的开创者和先锋人物。与马修斯同时代的另一位美国哲学家李普曼(Matthew Lipman)也是儿童哲学领域的奠基人,他们两人几乎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关注儿童与哲学之间的联系。他们的研究并非凭空跳出,而是基于20世纪对儿童的研究之上。当成年人不再把孩子看作“小大人”,不再用成年人的思维去理解孩子,儿童思维中跳跃的、难以捕捉的那些奇思妙想,反而逐渐吸引着成年人去反向思考儿童。
从1963年开始,马修斯陆续出版“儿童哲学三部曲”,把儿童与哲学关系的思考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虽然在书中列举了很多他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案例,但从教学实践上来说,他还并没有真正迈出那一步。将儿童哲学教育理念真正融入儿童课堂的是李普曼,他将儿童哲学归结为“Philosophy for Children”,也就是为儿童提供的一种哲学教育。在李普曼的实践下,儿童哲学的概念逐渐走出美国,扩散到英国、法国等更多西方国家。
中文世界里最早引入儿童哲学概念的是台湾学者,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者才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真正将哲学概念引入小学甚至幼儿园教育并逐渐形成气候,获得家长和孩子的认可,已是2010年之后的事了。因此,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教学实践来看,“儿童哲学”在中国仍是一个前沿的领域,充满了实验性和未来探索的空间。
那么,什么是儿童哲学?它与我们传统意义上认识的哲学学科之间,边界又在哪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童世骏是最早关注到儿童哲学领域的大陆学者之一,他告诉我,对儿童哲学的理解,philosophy和children是两个核心词,但两者之间用哪个介词来连接,是对儿童哲学产生不同理解的关键。如果给这个群体加以年龄的限制,还是集中在中学以下的群体。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童世骏(贾睿 摄)
马修斯将自己有关儿童哲学最重要的一本论著命名为“Philosophy of Childhood”,即《童年哲学》。他认为“儿童的哲学”和“成人的哲学”是相对的,正如成人有自己的哲学一样,儿童也有其自己的哲学。这里的哲学并不是教科书上晦涩难懂的哲学概念,也不是哲学大家的复杂的思辨,而是更近似于人生哲学、生活哲学。从马修斯和李普曼的理论发展而来,如今儿童哲学主要有四个面向的维度,即Philosophy for Children(给孩子的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ren(关于儿童成长的哲学思考)、Philosophy by Children(儿童对哲学的好奇和思考)、Philosophy with Children(与儿童一起进行的哲学探索)。
当我们站在成年人的角度,用学术的方式给儿童教育扣上了一个“哲学”的大帽子,并且设计诸多游戏、绘本、小说、课程来激发出孩子的哲学思维,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他们知道自己正在与哲学靠近吗?他们从儿童哲学中又能获得什么呢?这是我更好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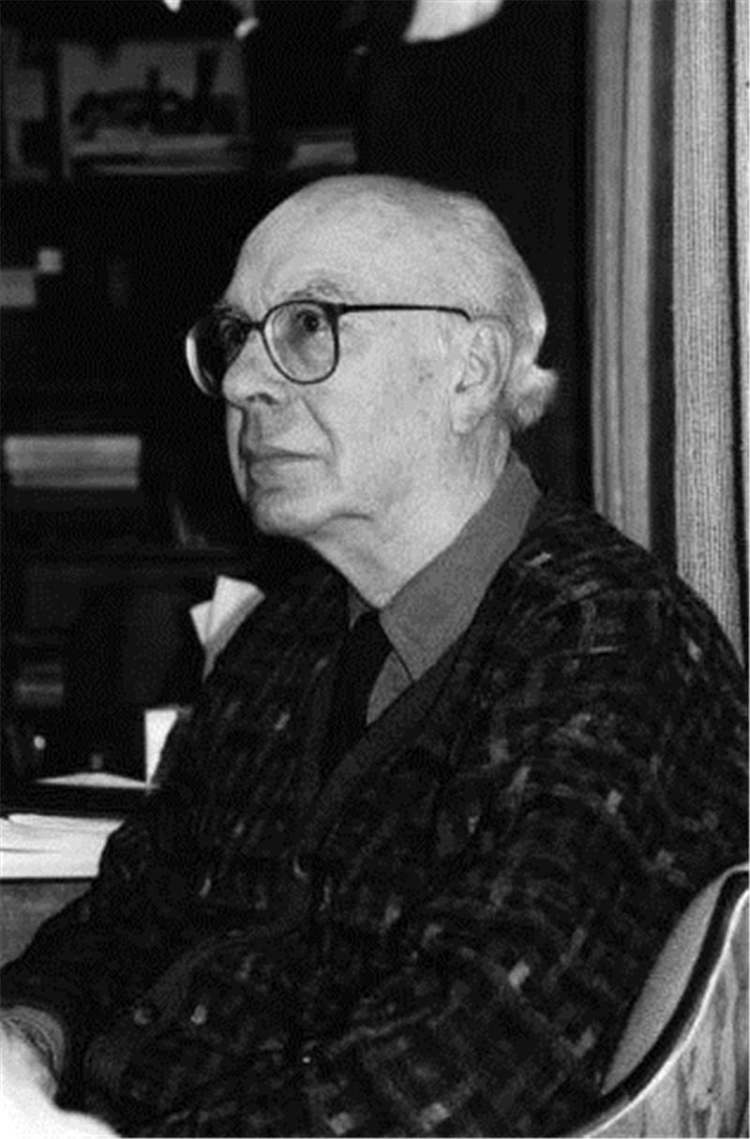
美国哲学家李普曼
没有一个问题是坏问题
现在接受儿童哲学教育的孩子通常是“10后”。“这是自我意识极其强烈的一代人,他们从小就有开阔的视野,生活中没有很多束缚,无论是言语自由的机会还是信息接触的机会,都是至今条件最优越的一代孩子。”李筱彤对我说。李筱彤从事儿童哲学教育已有五六年,目前在上海一所双语学校工作。在接受过英国儿童哲学更注重团体性和法国儿童哲学更注重批判性的教育之后,现在的她更认可美国夏威夷学派的理念,更具包容性、开放性,也可以更好地和东方思维相结合。
在双语学校的选修课制度下,当李筱彤带的小学生第一次上儿童哲学课时,有的孩子就会直接说:“老师,我上儿哲课的目的很简单,我听说上这个课可以把人变聪明,可以让人能言善辩,我想向人证明,我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这是一个极少数的让人哭笑不得的选课理由,也是很多老师的忧心“10后”会形成某种群体性特征——难以接纳不同的观点,丧失倾听的能力。
在李筱彤看来,倾听是儿童哲学的基础。因此,在进入真正的儿童哲学教育之前,必须要营造出一个“智力上的安全环境”,“因为很多话题是非常尖锐的,孩子们必须彼此信任,才能相互敞开,放下戒备,在一个彼此对等的环境下谈话,才能让谈话一步步地推进下去”。如果是小学阶段的孩子,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到两个月不等。而如果是幼儿园阶段,这个准备的过程可能贯穿始终,顺利的话,五六岁的孩子可以逐渐进入一个相对思辨的讨论环境中。
与李筱彤的做法相似,在幼儿园进行儿童哲学教育的郑国英老师也非常重视安全氛围的建设,她称之为“思维预热”。当老师和小孩围坐在一圈时,老师的权威感被降低,这个时候,规则的制定成为交流与思考的最重要前提。
在接触到儿童哲学领域之前,对于幼儿园的孩子学哲学这件事,我始终抱以将信将疑的态度,三五岁的孩子该如何与哲学发生关联呢?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指出,引发孩子的哲学性思维,通常需要一个刺激物,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用什么样的刺激物意味着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出孩子的想法。通常来说,越是低龄的孩子需要的刺激物越具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刺激物的抽象程度可以越来越高,直到他们有一定阅读文本的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贾睿 摄)
马修斯刚开始尝试将哲学引入儿童教育中时,他希望让孩子相信,“哲学是一项自然的活动(a natural activity),正像做音乐和玩游戏那样自然”。因此,儿童哲学其实与我们理解的大哲学家和哲学流派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一上来就跟孩子说,柏拉图是怎么理解的,叔本华又说了什么,这一点用都没有,只会让孩子觉得哲学与自己无关。而真正与他们相关的是哲学性的问题,诸如时间、朋友、自己、梦境这些,它们既可以构成哲学的底层问题,也是儿童经常发问的。
在3到7岁的儿童那里,这种自发性的哲学发问并不罕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发问会越来越少。马修斯认为,一旦儿童适应学校,他们便知道学校只期待提出“有用”的问题。于是,哲学思考要么走入地下——或许这些孩子会隐秘地继续在内心思索而不与他人分享,要么便处于完全休眠的状态。
当得知学校开设了儿童哲学的课程之后,并不会有家长真的期待自己的孩子未来会成为一个哲学家,而是期待这门课能够活跃孩子的思维。在童世骏看来,哲学的思考有两个来源,一是西方思维中的wonder,也就是产生惊讶的感觉,在古希腊的哲学环境中,惊讶、好奇成为很多思考与辩论的起点;另一个来源是忧患意识,它更像是中国哲学的土壤。由惊讶意识引发的哲学更注重自主性和自由,由忧患意识引发的思考则更注重人的责任感,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提升儿童的理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表达能力。
也正因为如此,儿童哲学可以是一门狭义上的具体课程,也可以是一个广义上的教育方法论。李普曼就认为哲学是一种黏合剂,可以帮助把所有独立的学科结合起来,这一点是更多儿童哲学教育的从业者希望看到的,哲学思维的训练应该是一以贯之的。

李筱彤和小朋友在画展上
跟孩子谈论死亡
对于每一个儿童哲学的老师来说,死亡都是那个最难展开的终极问题,一方面不知道孩子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怕孩子反弹回来的问题自己接不住,另一方面的压力则来自家长的质疑。
试图第一次跟孩子提到死亡之前,郑国英忐忑了很久。她是从动画片《寻梦环游记》进入的。但看这个动画片,对于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欢乐的事,即便是成年人看,也会触发内心有关亲情、死亡、善恶的终极思考。孩子能从动画片里看到什么?这个片子会成为孩子的噩梦吗,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吗?这都是令成人感到不安的。
《寻梦环游记》以墨西哥的亡灵节为背景,每逢这一天,去世亲人们的魂魄便可凭借着摆在祭坛上的照片返回现世和生者团圆。因为与生死相关,片中会出现大骷髅的场景。为了让大班的孩子适应这个场景,知道什么是骷髅,郑国英的第一课是带着孩子去自然博物馆看恐龙化石。当孩子们明白恐龙曾经主宰这个世界又灭绝了之后,人类找到它们的骨骼,收藏在博物馆中,来证明恐龙的存在与死亡,孩子们开始对那个远去的世代感到好奇。从恐龙的骨骼引申到人体的骨骼,孩子们开始对死亡有所认知。
郑国英本以为看《寻梦环游记》会成为这些五六岁孩子的第一节“死亡哲学教育课”,她为此做足了孩子们的心理建设,也预留出了充足的缓冲时间。但真正在幼儿园播放《寻梦环游记》时,孩子们的关注点却并不在骷髅或死亡上,而是在“反派”德拉库斯的谎言上。
德拉库斯通过一个个的谎言,将自己塑造成了片中的歌神,但当小男孩戳穿谎言,德拉库斯最终被大钟砸死,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因为撒谎而受到残酷的惩罚,这成为《寻梦环游记》给大班孩子印象最深的一幕。就像小维特根斯坦会对撒谎这个问题产生兴趣一样,“撒谎”是很多孩子接受的第一堂道德教育课,因而是与他们更密切相关的,死亡则不是。
郑国英告诉我,通常来说,五六岁的孩子会逐渐开始对死亡有概念,但这个概念深浅不一,当有真正的事件触发时,他们才会产生更直观的认知。她说与死亡相比,“不老”是更容易进入的话题。我们会永远都不变老吗?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老,会发生什么?是不是就不会面对死亡了?——当这些与死亡相关的间接问题摆在孩子面前,他们更容易理解,因为大多数孩子见过老人,却没见过死亡的人,这属于他们的“儿童经验”范畴。
在上海另一所民办学校教授儿哲课的颜志豪,他面对的是三四年级以上的孩子。颜志豪也给自己的学生看了《寻梦环游记》,在他看来,这些孩子已经对“after life”有所意识了,也就是身后事。在讨论到生命哲学或是生与死的话题时,他会将具体的人的生死抽离出来,放到更宏观的自然界的生死轮回中去引导,秋天的落叶、死去的小动物,都可以将话题引向生死。
然而颜志豪非常不主张“爷爷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这种说法,当亲人的死亡真正摆在孩子的面前时,是一堂最好的哲学课。李筱彤也告诉我,她不会随便去给孩子讲死亡,但是当真的死亡摆在面前时,“为什么要回避呢?这是一个多好的教育素材”。
哲学教育的收效是非常缓慢的,但日积月累之后,孩子的身上是会发展变化的。李筱彤曾经给四年级的学生讲过死亡,探讨为什么死亡会让人恐惧,明明没有人真正感受过死亡,大家到底在害怕什么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大概两三年后,班里一个台湾孩子的外婆去世,他从上海回台湾,在临终病房里见到了外婆最后一面,他握着外婆的手跟外婆说了很多安慰的话,让外婆不要害怕,让她平静,让她安宁地离开。小男孩好像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外婆做他力所能及的一种临终关怀。这一次之后,他对死亡有了更深的感受力。
儿童哲学是一件交互的事,由儿童、老师、家长基于对话和思考共同完成,很难由儿童独立进展下去。它既是一个哲学领域的事,也是一个教育问题,“哲学”与“教育”的比重几乎均等。李筱彤告诉我,在这个过程中,老师的角色很重要,既需要有一线教育的背景,懂得儿童在想什么,知道该怎么用孩子可以接纳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又需要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在熟悉哲学思考的逻辑思维之后,将这种思维转化到与儿童的交流中,如何引导而不是强制性地灌输,又能接得住孩子抛出的古怪问题,是对儿童哲学教师的巨大考验。
而一旦进入这个角色,儿童往往会成为成年人的一面镜子,折射出诸多不曾思考过的问题。颜志豪在第一节儿童哲学课上,会让孩子们写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尽可能多地去写,再由全班共同投票,选出10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比如宇宙是怎么起源的?宇宙有没有边界?圣诞老人真的存在吗?在上过一段时间哲学课之后,颜志豪问他的学生,现在你们觉得什么是哲学?他收到的这些答案足以让他对哲学产生更深的反思:
“哲学,就是困难的问题。”
“哲学是可怕的问题,像《黑客帝国》里面的情景一样,像很深的黑坑。”
“哲学,就是答案里面的答案,要对那些已经有表面答案的问题找深层的答案。”
“哲学,就是通过合作和讨论,给其他人的观点挑错,然后接近答案。”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